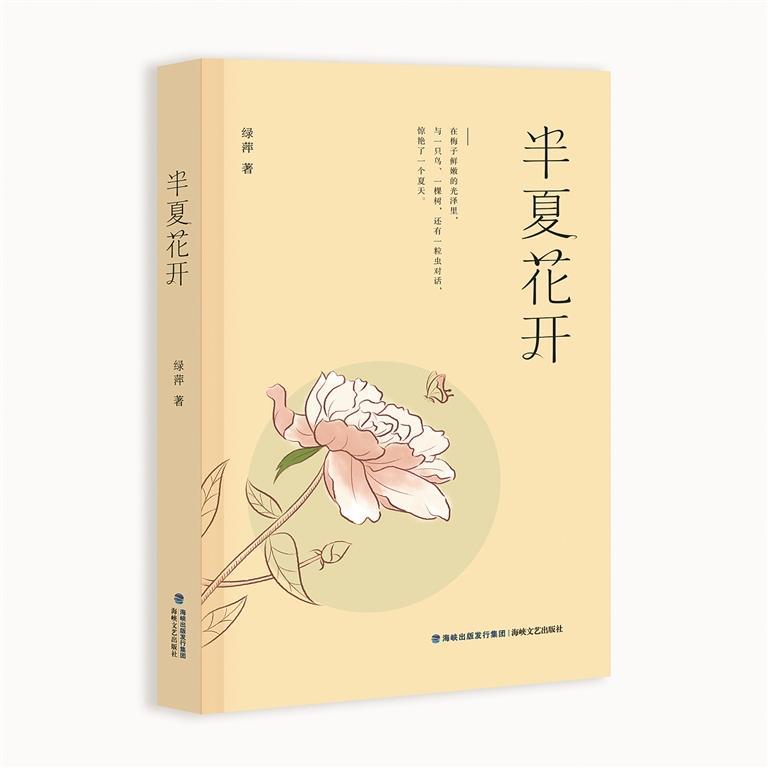■陈伯强
绿萍是生长在水田或池塘中的小型浮水植物,广泛生长于我国南北方的水域中。“春雨生绿萍,秋风梦红蓼”,是颇有意境的。
有一个阶段,我曾经为找不到“绿萍”的合适量词而苦恼。我们知道,在汉字中,量词有明显的表形作用,运用量词可以突出表现事物的主要形态特征。关于绿萍,用“枚”则太普通;用“朵”则太庞大;用“株”吧,她没有根基;用“条”吧,她又非长条形。勉强可用的是“叶”,但绿萍跟树叶有着显著的区别,只是类似树叶,而且又漂浮不定。
无法用量词准确表现一个事物,让我很是恐慌。唐代诗人卢延让说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和清代诗人袁枚说的“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大概就是这种情形。
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我们需要确定性。对于一个事物,如果没办法恰当地去描述和命名它,我是大恐慌的。《老子》第十四章:“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一旦一种事物不可以用语言描述,或者被命名,那么人们就不容易感受到自己和它之间发生的奇妙联系,也就无法让我们更清晰地意识到它的存在并感受到它。
绿萍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捉摸不定的女子。她在生活中,叫庄丽萍,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女人,一个普通的惠安女子。而在作品中,她则叫“绿萍”,漂浮不定,摇曳生姿,让人捉摸不透。
绿萍出版过三本书。第一本《说好秋天就成熟》,我给她写了一篇《成熟的女人韵最美》的评介文章;第二本《在春天奔跑》,我又为她写过《她从诗经走来》的评析文章。现在,她的第三本书《半夏花开》摆在我的案前,我却茫然而无从下笔。
作为绿萍的忠实铁杆粉丝,我的眼光追随着她,脚步紧随着她。但在《半夏花开》这本书前,我的眼光迷离了,脚步凌乱了。《半夏花开》确实让我震撼——在我眼里曾经的“小女子”,华丽丽地转身了。与之前的小女子散文不同,《半夏花开》思域宽阔,气势恢宏,纵横驰骋,表现手法老到,显得很成熟——而我说过,成熟的女人韵最美。
《半夏花开》这本书,摒弃了小格局小视野小情调,展现大视野大格局大情怀。大视野带着大格局,大格局书写大手笔,大手笔挥洒大情怀。
首先引起我关注的是书中的一些长篇散文,如《痕迹》《树下》《夜行者》《游移的花朵》。我们知道,散文一般以短小见长。在快阅读时代,写长篇散文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大家都那么忙,谁有闲工夫看你的长篇大论呢?散文当是于茶余饭后,三五分钟便可读完一篇的,若是你把一件事情或者东西从头到尾、细枝末节地叙述清楚明白,开始高潮结尾都一一展开,那它便不是散文,而是小说了。
因此,长篇散文是很考验一个作家的功力的。丰富的经历,多元化体验与深刻的感受,以及匠心独运的构思、娴熟的文字驾驭能力,都是写长篇散文不可缺少的要件。真的,把文章写“长”是一个作家很重要的能力,是很考验功底的。比如《痕迹》一文,作者从毕业分配表、实习期鉴定表、申报各种职称的表格的失而复得说起,写到老家族谱的修订、祖父的家书、古人的手迹、九日山祈风石刻、杨凝式的《韭花帖》、自己上课时喜欢板书等,以“痕迹”为主题,上下勾连,旁枝逸出,却不离“岁月留痕”这个主题。
人生的厚重正是岁月阅历累积沉淀下来的,厚重的人生才有厚重的散文表达。流年飞度,岁月更迭,时间赠人阅历,散文写成这个样子,仿佛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从小散文到大散文,不仅仅是篇幅上的大,而是更多表现在内容的深度开掘上。绿萍的散文更多的是关注日常,正如她在后记中所说:“选材范围狭促,过于细致甚至絮叨等等,都是天生致命的弱点,我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也努力尝试着探索与规避……”但她善于从日常的琐碎中深度挖掘,不断去丰富生活的内涵,从而在内容上有很大的拓展,把文章写得饱满、生动、鲜活,使文章具有张力。她站在低处生活,站在高处思考。如《游移的花朵》一文,从惠安女的黄斗笠写起,写到祖父的油纸伞,到补伞匠,到补伞匠这个行当的没落,写的是伞,见证的是一个时代的变迁。《半夏花开》中,不乏这样的匠心之作,如《白云生处》《街声》《小坐》都是落脚小处,着眼远方,言近而旨远。这些文章,选材虽小,但开掘纵深,颇见营造腾挪之功力、匠心独运之巧思。鲁迅认为,文章“选材要严,开掘要深”,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好的散文作家要写出有价值、正能量、大情怀的作品,就不能只是从狭隘的日常琐碎中选材,并满足于自己的小情调小情怀,而是必须突破自己狭隘的生命和个体情感的有限体验意识,将人文精神、理性思维、史学修养、社会关怀、文化批判、宗教文化等纳入个人写作的元素和参考之中,这样创作的作品才会体现出不同于一般写作的生命价值和自觉文化的担当。
《半夏花开》是绿萍写作上的一个转折,是小女子散文向大散文的嬗变。她挣脱“肤浅”,走向“深刻”;挣脱“幼稚”,走向“成熟”;挣脱“造作”,走向“自然”。
“半夏”是个美丽的名字,“花开”也是。半夏花开,开一季璀璨,绽无限风采。
苔米如花,绿萍如粟。
绿萍,可以是一叶,还可以是一株,当然也可以是一池一湖的。
绿萍,多个量词,多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