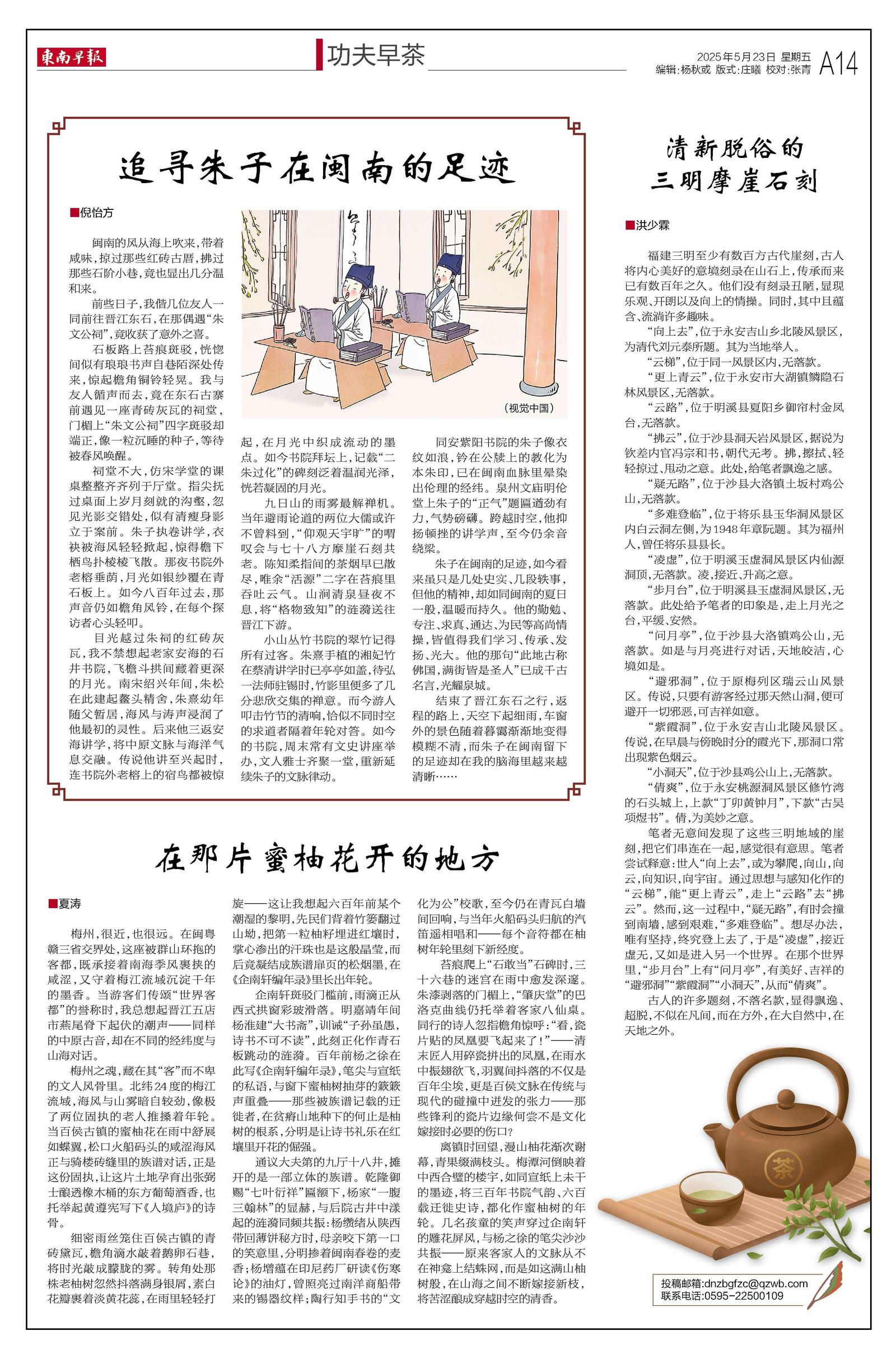■夏涛
梅州,很近,也很远。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处,这座被群山环抱的客都,既承接着南海季风裹挟的咸涩,又守着梅江流域沉淀千年的墨香。当游客们传颂“世界客都”的誉称时,我总想起晋江五店市燕尾脊下起伏的潮声——同样的中原古音,却在不同的经纬度与山海对话。
梅州之魂,藏在其“客”而不卑的文人风骨里。北纬24度的梅江流域,海风与山雾暗自较劲,像极了两位固执的老人推搡着年轮。当百侯古镇的蜜柚花在雨中舒展如蝶翼,松口火船码头的咸涩海风正与骑楼砖缝里的族谱对话,正是这份固执,让这片土地孕育出张弼士酿透橡木桶的东方葡萄酒香,也托举起黄遵宪写下《人境庐》的诗骨。
细密雨丝笼住百侯古镇的青砖黛瓦,檐角滴水敲着鹅卵石巷,将时光敲成朦胧的雾。转角处那株老柚树忽然抖落满身银屑,素白花瓣裹着淡黄花蕊,在雨里轻轻打旋——这让我想起六百年前某个潮湿的黎明,先民们背着竹篓翻过山坳,把第一粒柚籽埋进红壤时,掌心渗出的汗珠也是这般晶莹,而后竟凝结成族谱扉页的松烟墨,在《企南轩编年录》里长出年轮。
企南轩斑驳门槛前,雨滴正从西式拱窗彩玻滑落。明嘉靖年间杨淮建“大书斋”,训诫“子孙虽愚,诗书不可不读”,此刻正化作青石板跳动的涟漪。百年前杨之徐在此写《企南轩编年录》,笔尖与宣纸的私语,与窗下蜜柚树抽芽的簌簌声重叠——那些被族谱记载的迁徙者,在贫瘠山地种下的何止是柚树的根系,分明是让诗书礼乐在红壤里开花的倔强。
通议大夫第的九厅十八井,摊开的是一部立体的族谱。乾隆御赐“七叶衍祥”匾额下,杨家“一腹三翰林”的显赫,与后院古井中漾起的涟漪同频共振:杨缵绪从陕西带回薄饼秘方时,母亲咬下第一口的笑意里,分明掺着闽南春卷的麦香;杨增蕴在印尼药厂研读《伤寒论》的油灯,曾照亮过南洋商船带来的锡器纹样;陶行知手书的“文化为公”校歌,至今仍在青瓦白墙间回响,与当年火船码头归航的汽笛遥相唱和——每个音符都在柚树年轮里刻下新经度。
苔痕爬上“石敢当”石碑时,三十六巷的迷宫在雨中愈发深邃。朱漆剥落的门楣上,“肇庆堂”的巴洛克曲线仍托举着客家八仙桌。同行的诗人忽指檐角惊呼:“看,瓷片贴的凤凰要飞起来了!”——清末匠人用碎瓷拼出的凤凰,在雨水中振翅欲飞,羽翼间抖落的不仅是百年尘埃,更是百侯文脉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迸发的张力——那些锋利的瓷片边缘何尝不是文化嫁接时必要的伤口?
离镇时回望,漫山柚花渐次谢幕,青果缀满枝头。梅潭河倒映着中西合璧的楼宇,如同宣纸上未干的墨迹,将三百年书院气韵、六百载迁徙史诗,都化作蜜柚树的年轮。几名孩童的笑声穿过企南轩的雕花屏风,与杨之徐的笔尖沙沙共振——原来客家人的文脉从不在神龛上结蛛网,而是如这满山柚树般,在山海之间不断嫁接新枝,将苦涩酿成穿越时空的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