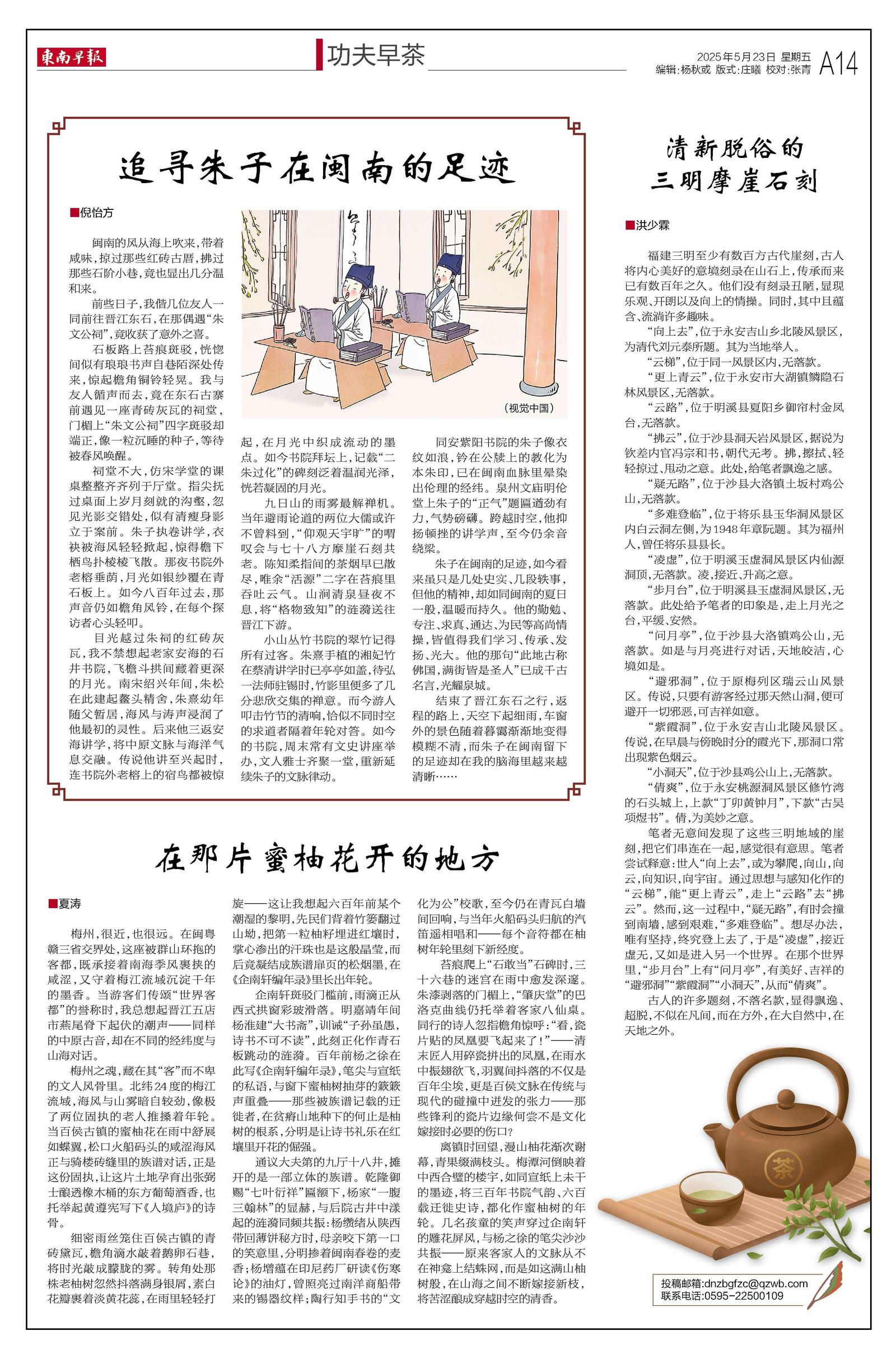■倪怡方
闽南的风从海上吹来,带着咸味,掠过那些红砖古厝,拂过那些石阶小巷,竟也显出几分温和来。
前些日子,我偕几位友人一同前往晋江东石,在那偶遇“朱文公祠”,竟收获了意外之喜。
石板路上苔痕斑驳,恍惚间似有琅琅书声自巷陌深处传来,惊起檐角铜铃轻晃。我与友人循声而去,竟在东石古寨前遇见一座青砖灰瓦的祠堂,门楣上“朱文公祠”四字斑驳却端正,像一粒沉睡的种子,等待被春风唤醒。
祠堂不大,仿宋学堂的课桌整整齐齐列于厅堂。指尖抚过桌面上岁月刻就的沟壑,忽见光影交错处,似有清瘦身影立于案前。朱子执卷讲学,衣袂被海风轻轻掀起,惊得檐下栖鸟扑棱棱飞散。那夜书院外老榕垂荫,月光如银纱覆在青石板上。如今八百年过去,那声音仍如檐角风铃,在每个探访者心头轻叩。
目光越过朱祠的红砖灰瓦,我不禁想起老家安海的石井书院,飞檐斗拱间藏着更深的月光。南宋绍兴年间,朱松在此建起鳌头精舍,朱熹幼年随父暂居,海风与涛声浸润了他最初的灵性。后来他三返安海讲学,将中原文脉与海洋气息交融。传说他讲至兴起时,连书院外老榕上的宿鸟都被惊起,在月光中织成流动的墨点。如今书院拜坛上,记载“二朱过化”的碑刻泛着温润光泽,恍若凝固的月光。
九日山的雨雾最解禅机。当年避雨论道的两位大儒或许不曾料到,“仰观天宇旷”的喟叹会与七十八方摩崖石刻共老。陈知柔指间的茶烟早已散尽,唯余“活源”二字在苔痕里吞吐云气。山涧清泉昼夜不息,将“格物致知”的涟漪送往晋江下游。
小山丛竹书院的翠竹记得所有过客。朱熹手植的湘妃竹在蔡清讲学时已亭亭如盖,待弘一法师驻锡时,竹影里便多了几分悲欣交集的禅意。而今游人叩击竹节的清响,恰似不同时空的求道者隔着年轮对答。如今的书院,周末常有文史讲座举办,文人雅士齐聚一堂,重新延续朱子的文脉律动。
同安紫阳书院的朱子像衣纹如浪,钤在公牍上的教化为本朱印,已在闽南血脉里晕染出伦理的经纬。泉州文庙明伦堂上朱子的“正气”题匾遒劲有力,气势磅礴。跨越时空,他抑扬顿挫的讲学声,至今仍余音绕梁。
朱子在闽南的足迹,如今看来虽只是几处史实、几段轶事,但他的精神,却如同闽南的夏日一般,温暖而持久。他的勤勉、专注、求真、通达、为民等高尚情操,皆值得我们学习、传承、发扬、光大。他的那句“此地古称佛国,满街皆是圣人”已成千古名言,光耀泉城。
结束了晋江东石之行,返程的路上,天空下起细雨,车窗外的景色随着暮霭渐渐地变得模糊不清,而朱子在闽南留下的足迹却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