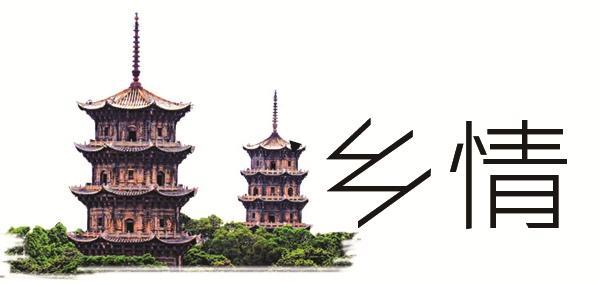周末带着儿子回老家,他执意要去新修的公路耍一耍。
老家在半山腰,说是新修的路,其实不然,只是在原有的山路上,裁弯取直,铺上水泥,更宽敞,更便于通行。山路从村口的小水塘开始,沿着山坡倾斜而下,像是崭新的领带打在脖颈上,村庄顿时精神了很多。
儿子快意冲坡,时不时喊我一起加速。他不满六岁,待在村子的时间不超过六个月,这条路对他来说是陌生而新奇的。
儿子在草丛里捡到一个废弃的矿泉水瓶,俯身去溪流里盛满水。他本想抓一条鱼,可惜没能如愿,坐在路边很是失落。我逮了一只蝉放到瓶子里,他渐渐有了笑容。一只、两只、三只……我们抓了一把。休息的时候,儿子告诉我,他的矿泉水瓶是世界上最大的容器,能放得下许许多多的蝉,并善意地问:“爸爸携带的最大容器是什么?”
带着一瓶子的鸣蝉继续冲坡,他好奇地问我:“前面有什么?”我说前面那一段路有我的童年。九岁开始,我沿着这条路下山,到邻村小学读书,每日往返。我开始讲述我在这条路上的故事。求学的路上,我得到村里人很多帮助。有一次,放学比较迟,匆忙赶路,在山路的拐弯处把脚给崴了。村里的一个小伙子刚好路过,把我从山下背回了家。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他汗涔涔的样子,还有那温暖的后背和肩膀。
再前面呢?儿子还想往下走,他指的方向,是路边一片荒废的稻田。那是你爷爷的倔强!那个地方曾经是我们家找别人租来耕种的田地。父亲是个教书匠,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的工资不足以养活我们一家。于是他和母亲合计着找人租了块地,花生和水稻交替耕种。临近山路,耕作起来比较方便。父亲教书之余,每天夕阳下山的时候,一定会去田里走走看看。他说,人身上有气味,野猪能嗅到,不敢来破坏农作物。我没有求证过真假,但,父亲确实靠着这股倔强,把我们兄弟三人带出这个村庄。
再往前呢?我看不清孩子所指的具体位置,隐约看出几个小草堆。只有熟悉这条山路的人才知道,那是坟茔。那一段有你太爷爷的温情!我脱口而出。这件事情,我曾经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讲过。那年新来的邻家孩子发高烧,男主人外出讨生活,女主人独自背着孩子沿着这条路下山求医。山路边上一方方矮矮的坟墓,阴冷不已,走这样的夜路,是不安的,是惶恐的。爷爷打着手电筒,把她们母子带出崎岖的山路,走出漆黑的夜。爷爷去世那天,她哭着把这个故事讲给所有人听。
回忆有时候真像蝉,总是“知了知了”地叫个不停,让人越陷越深。被儿子从瓶子里倒出来的水,把水泥路面洇湿了,我们挪了下位置继续在路面上聊天。
再往前呢?再往前就走出大山了,那是泉州市区的方向,那是你的童年。相比这个小村庄,儿子更熟悉那座城市。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时间如地面上的流水,把很多东西稀释得让人品不出原本的滋味,就连最熟悉的路也换了新装。山风落叶理解我这种惆怅,在衣襟领口轻轻抚慰。幸运的是,绿野平畴还是我恩人,鸟声花影依然是我知己,残石废垒仍旧是我故交。
我的容器可能就是一条山路吧!它收集了祖祖辈辈的脚步,然后把它们拓印在我们的胸口,画成一个圆,不起眼的圆心,我称之为故乡。怎么跟一个不满六岁的小孩解释山路也是一种容器呢?看着他的瓶子,我说,我带了一个看不见的容器,也装满了知了,此刻,它们在心中叫得正欢。
黼黻的文字,难于形容内心对家乡那份天生的亲近。我拿起手机拍了一张孩子的背影,或许成长就是这样,他在前面走着,我在后面追着,慢慢地,他离我越来越远,像我离家乡越来越远一样。我们都是瓶子里的鸣蝉,迥异之处在于,它们是被我抓到瓶子里的,而我是主动进入这个叫家乡的瓶子。
村里募捐资金给这条山路安装路灯,四叔帮我们兄弟姐妹各捐了一盏,为出行提供一点光亮,也点亮那些回家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