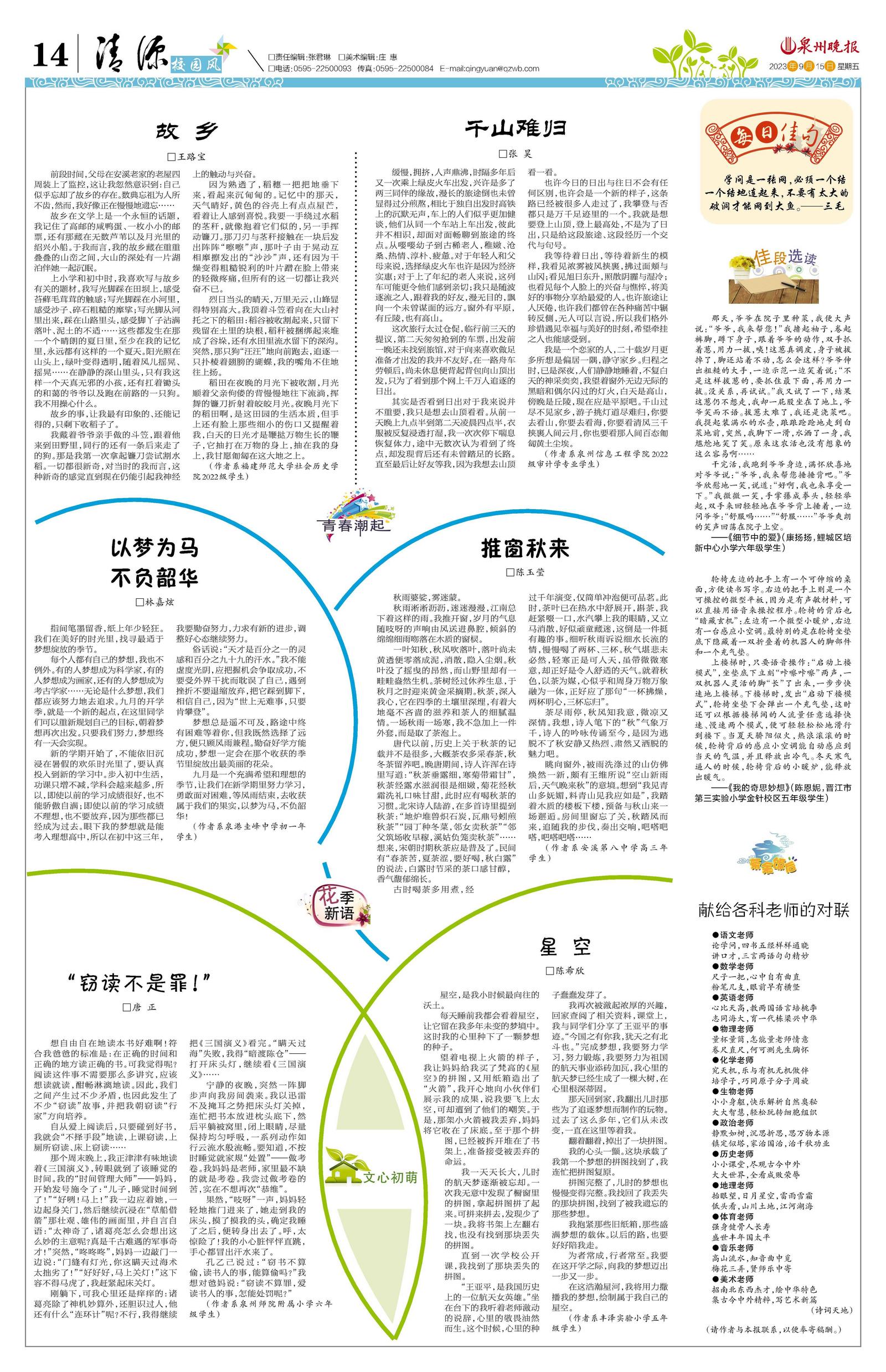□王路宝
前段时间,父母在安溪老家的老屋四周装上了监控,这让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似乎忘却了故乡的存在。数典忘祖为人所不齿,然而,我好像正在慢慢地遗忘……
故乡在文学上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记住了高邮的咸鸭蛋、一枚小小的邮票,还有那藏在无数芦苇以及月光里的绍兴小船。于我而言,我的故乡藏在重重叠叠的山峦之间,大山的深处有一片湖泊伴她一起沉眠。
上小学和初中时,我喜欢写与故乡有关的题材。我写光脚踩在田坝上,感受苔藓毛茸茸的触感;写光脚踩在小河里,感受沙子、碎石粗糙的摩挲;写光脚从河里出来,踩在山路里头,感受脚丫子沾满落叶、泥土的不适……这些都发生在那一个个晴朗的夏日里,至少在我的记忆里,永远都有这样的一个夏天。阳光照在山头上,绿叶变得透明,随着风儿摇晃、摇晃……在静静的深山里头,只有我这样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还有扛着锄头的和蔼的爷爷以及跑在前路的一只狗。我不用操心什么。
故乡的事,让我最有印象的、还能记得的,只剩下收稻子了。
我戴着爷爷亲手做的斗笠,跟着他来到田野里,同行的还有一条后来走了的狗。那是我第一次拿起镰刀尝试割水稻。一切都很新奇,对当时的我而言,这种新奇的感觉直到现在仍能引起我神经上的触动与兴奋。
因为熟透了,稻穗一把把地垂下来,看起来沉甸甸的。记忆中的那天,天气晴好,黄色的谷壳上有点点星芒,看着让人感到喜悦。我要一手绕过水稻的茎秆,就像抱着它们似的,另一手挥动镰刀。那刀刃与茎秆接触在一块后发出阵阵“嚓嚓”声,那叶子由于晃动互相摩擦发出的“沙沙”声,还有因为干燥变得粗糙锐利的叶片蹭在脸上带来的轻微疼痛,但所有的这一切都让我兴奋不已。
烈日当头的晴天,万里无云,山峰显得特别高大。我顶着斗笠看向在大山衬托之下的稻田:稻谷被收割起来,只留下残留在土里的块根,稻秆被捆绑起来堆成了谷垛,还有水田里流水留下的深沟。突然,那只狗“汪汪”地向前跑去,追逐一只扑棱着翅膀的蝴蝶,我的嘴角不住地往上扬。
稻田在夜晚的月光下被收割,月光顺着父亲佝偻的背慢慢地往下流淌,挥舞的镰刀折射着皎皎月光。夜晚月光下的稻田啊,是这田园的生活本质,但手上还有脸上那些细小的伤口又提醒着我,白天的日光才是鞭挞万物生长的鞭子,它抽打在万物的身上,抽在我的身上,我甘愿匍匐在这大地之上。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2022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