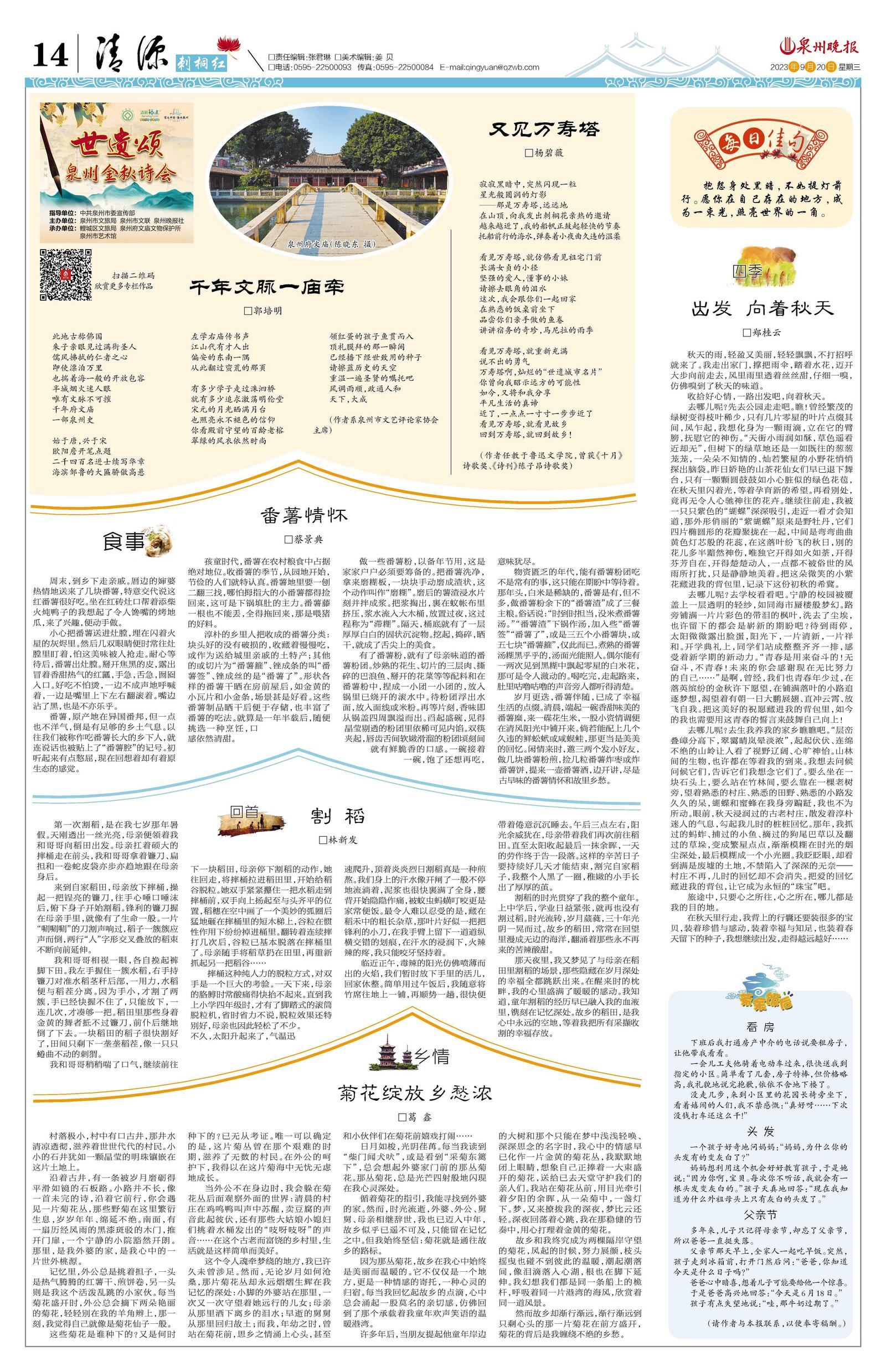□蔡景典
周末,到乡下走亲戚。厝边的婶婆热情地送来了几块番薯,特意交代说这红番薯很好吃。坐在红砖灶口帮着添柴火炖鸭子的我想起了令人馋嘴的烤地瓜,来了兴趣,便动手做。
小心把番薯送进灶膛,埋在闪着火星的灰烬里。然后几双眼睛便时常往灶膛里盯着,怕这美味被人抢走。耐心等待后,番薯出灶膛。掰开焦黑的皮,露出冒着香甜热气的红瓤,手急,舌急,囫囵入口。好吃不怕烫,一边不成声地呼喊着,一边是嘴里上下左右翻滚着。嘴边沾了黑,也是不亦乐乎。
番薯,原产地在异国番邦,但一点也不洋气,倒是有足够的乡土气息。以往我们被称作吃番薯长大的乡下人,就连说话也被贴上了“番薯腔”的记号。初听起来有点憋屈,现在回想着却有着原生态的感觉。
孩童时代,番薯在农村粮食中占据绝对地位。收番薯的季节,从园地开始,节俭的人们就特认真。番薯地里要一刨二翻三找,哪怕拇指大的小番薯都得捡回来,这可是下锅填肚的主力。番薯藤一根也不能丢,全得拖回来,那是喂猪的好料。
淳朴的乡里人把收成的番薯分类:块头好的没有破损的,收藏着慢慢吃,或作为送给城里亲戚的土特产;其他的或切片为“番薯箍”、锉成条的叫“番薯签”、锉成丝的是“番薯了”。形状各样的番薯干晒在房前屋后,如金黄的小瓦片和小金条,场景甚是好看。这些番薯制品晒干后便于存储,也丰富了番薯的吃法。就算是一年半载后,随便挑选一种烹饪,口感依然清甜。
做一些番薯粉,以备年节用,这是家家户户必须要筹备的。把番薯洗净,拿来磨糊板,一块块手动磨成渣状,这个动作叫作“磨糊”。磨后的薯渣浸水片刻并拌成浆。把浆掏出,裹在蚊帐布里挤压,浆水流入大木桶,放置过夜,这过程称为“滞糊”。隔天,桶底就有了一层厚厚白白的固状沉淀物。挖起,捣碎,晒干,就成了舌尖上的美食。
有了番薯粉,就有了母亲味道的番薯粉团。炒熟的花生、切片的三层肉、撕碎的巴浪鱼、掰开的花菜等等配料和在番薯粉中,捏成一小团一小团的,放入锅里已烧开的滚水中。待粉团浮出水面,放入面线或米粉。再等片刻,香味即从锅盖四周飘溢而出。舀起盛碗,见得晶莹剔透的粉团里依稀可见内馅。双筷夹起,唇齿舌间软嫩滑溜的粉团顷刻间就有鲜脆香的口感。一碗接着一碗,饱了还想再吃,意味犹尽。
物资匮乏的年代,能有番薯粉团吃不是常有的事,这只能在期盼中等待着。那年头,白米是稀缺的,番薯是有,但不多,做番薯粉余下的“番薯渣”成了三餐主粮。俗话说:“时到时担当,没米煮番薯汤。”“番薯渣”下锅作汤,加入些“番薯签”“番薯了”,或是三五个小番薯块,或五七块“番薯箍”,仅此而已。煮熟的番薯汤糊黑乎乎的,汤面光能照人。偶尔能有一两次见到黑糊中飘起零星的白米花,那可是令人激动的。喝吃完,走起路来,肚里咕噜咕噜的声音旁人都听得清楚。
岁月更迭,番薯伴随,已成了幸福生活的点缀。清晨,端起一碗香甜味美的番薯糜,来一碟花生米,一股小资情调便在清风阳光中铺开来。倘若能配上几个久违的鲜蚣蚮或咸蚬鲑,那更当是美美的回忆。闲情来时,邀三两个发小好友,做几块番薯粉煎,捡几粒番薯炸枣或炸番薯饼,提来一壶番薯酒,边开讲,尽是古早味的番薯情怀和故里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