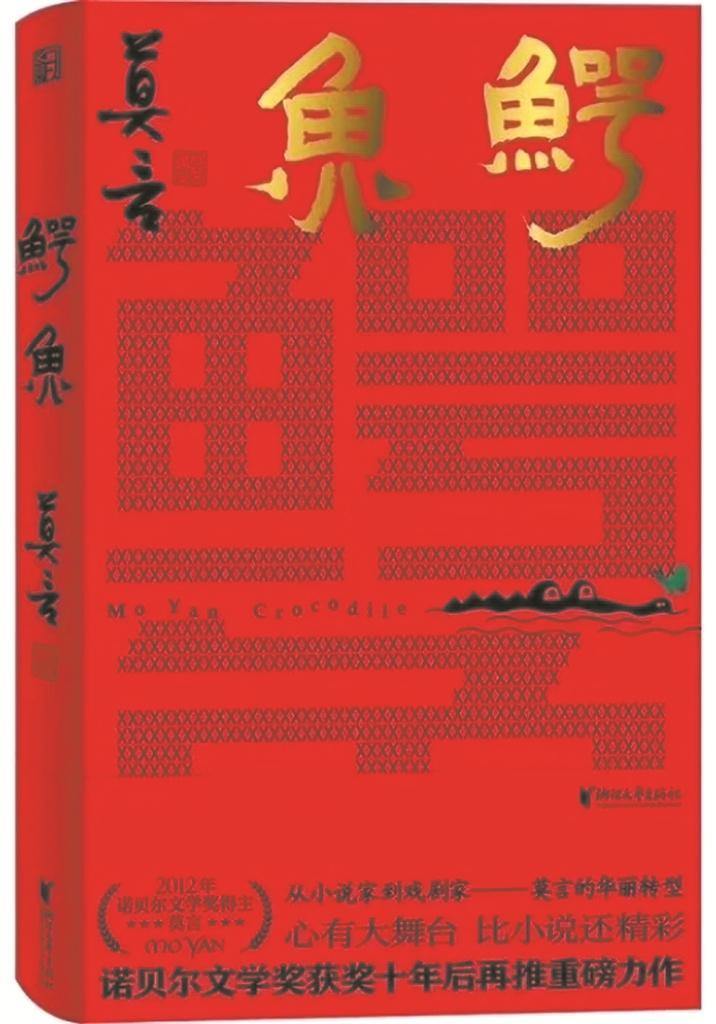□任诗桐
小说家莫言自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除2020年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外,更多地是以创作古体诗及书法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新作《鳄鱼》则用四幕话剧剧本的方式,实现了其从小说家向剧作家的转型。细读文本,我们发现在表现形式变化之外,一以贯之的是对人性的透视与批判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
剧作共四幕九场,以逃往海外的贪官单不惮在五十五岁生日收到寿礼“鳄鱼”开篇,借助与其妻子、情人、下属等角色之间关系的演绎,运用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的手法,通过一条随着环境变化能够无限生长、会说人话的鳄鱼,揭示了由“欲望”滋生出的贪婪对人性的腐蚀。
从某种意义上看,剧本通常都是通过台词展现人物关系来推进故事的发展,这与小说的叙述性和诗歌的抒情性截然不同。在《鳄鱼》中,以主人公单不惮为核心,作者构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妻子吴巧玲与情人马秀花各有所图,纠缠不已。单不惮与吴巧玲有名无实,与马秀花有实无名,吴巧玲与马秀花则为了争夺房产,狭路相逢,争论不休。一个虽为法妻,但得不到丈夫的爱;一个侍奉左右,却总也不能获取名分。刘慕飞与魏局长,均是单不惮的下属,前者好赌,寄生在单不惮身边与马秀花有染最后私奔;后者准备回国自首前,希望单不惮也做出同样选择,实则是为了通过监视其行踪而作为立功的表现。“他人即地狱”,每一个个体都想要按照自我意志试图控制他人,在如此的拉扯与相互控制中,逐渐迷失了自我。莫言通过几组人物关系的呈现,探讨了人类难以摆脱的生存困境。
小说和戏剧同属文学四大体裁,但剧作家必须具备戏剧性思维,即可为演员的表演提供可能性,这是戏剧和小说最大的不同。而在阅读的维度上,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和人性真相的揭示则是两种文学样式的共同之处。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演变中,反腐题材的文学作品并不少见,周梅森、王跃文、周大新等均有精品力作,他们大多着重于对官场浮世绘的描写。莫言在《鳄鱼》中则开辟了一条新路,刻画了一位逃亡海外的贪腐官员,其笔墨没有放在腐败的过程和细节,而是着眼于心理和精神层面的挖掘。
回首当年,单不惮也曾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对于乡亲的照顾他铭记有心,“我至今还记得她那同情的、殷切的眼神。当时我就暗暗叮嘱自己:如果有朝一日混好了,一定要好好报答这位姐姐。”身处国外,他无比思念家乡,然而,欲望终于还是如那条神奇的鳄鱼般,不断生长成为身长4米的庞然巨兽,如同巨大的漩涡,让人深陷其中,自食恶果。在最后一幕中,作者用大段台词展现了单不惮的追悔莫及:“如果没有这些事,那我可以把青云大桥建成优质工程,百年不摇,千年不塌……如果没有欲望的泛滥,我一定是一个能为人民群众带来福祉的好官,被人民夸奖,被人民感谢,那时多么荣耀、多么幸福!”通过台词,莫言着力塑造的是一个立体复杂的贪官形象。
莫言在剧作中仍延续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剧作中,鳄鱼深具象征意蕴。它虽为“世界上最为珍稀的奥里诺科鳄鱼,全世界的野生存量不过两百条”,但起初它也不过三十厘米,如果只在狭小的空间里它并不会长大,单不惮却不断地为其更换越来越大的鱼缸,直至其长成一具庞然大物,就如同他控制不住的欲望。最终,开口说话的鳄鱼与单不惮合二为一,完成了来自欲望的自我审判:“单无惮,六十五岁,逃亡贪官。作恶多端但良心未泯。畏罪逃亡却热爱祖国。喜欢女人却终被女人抛弃。满怀壮志却一事无成。放纵欲望导致家破人亡。豢养鳄鱼最终葬身鳄鱼之腹。”
有人说,转型戏剧创作源自莫言担心自己将囿于“诺贝尔文学奖魔咒”,即获奖作家会在获奖之后,不再能持续创作出经典佳作。转型也好,魔咒也罢,变化的只是体裁和表现形式,对人的关注依然是文学永恒不变的主题,不变的仍旧是对人类命运和情感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