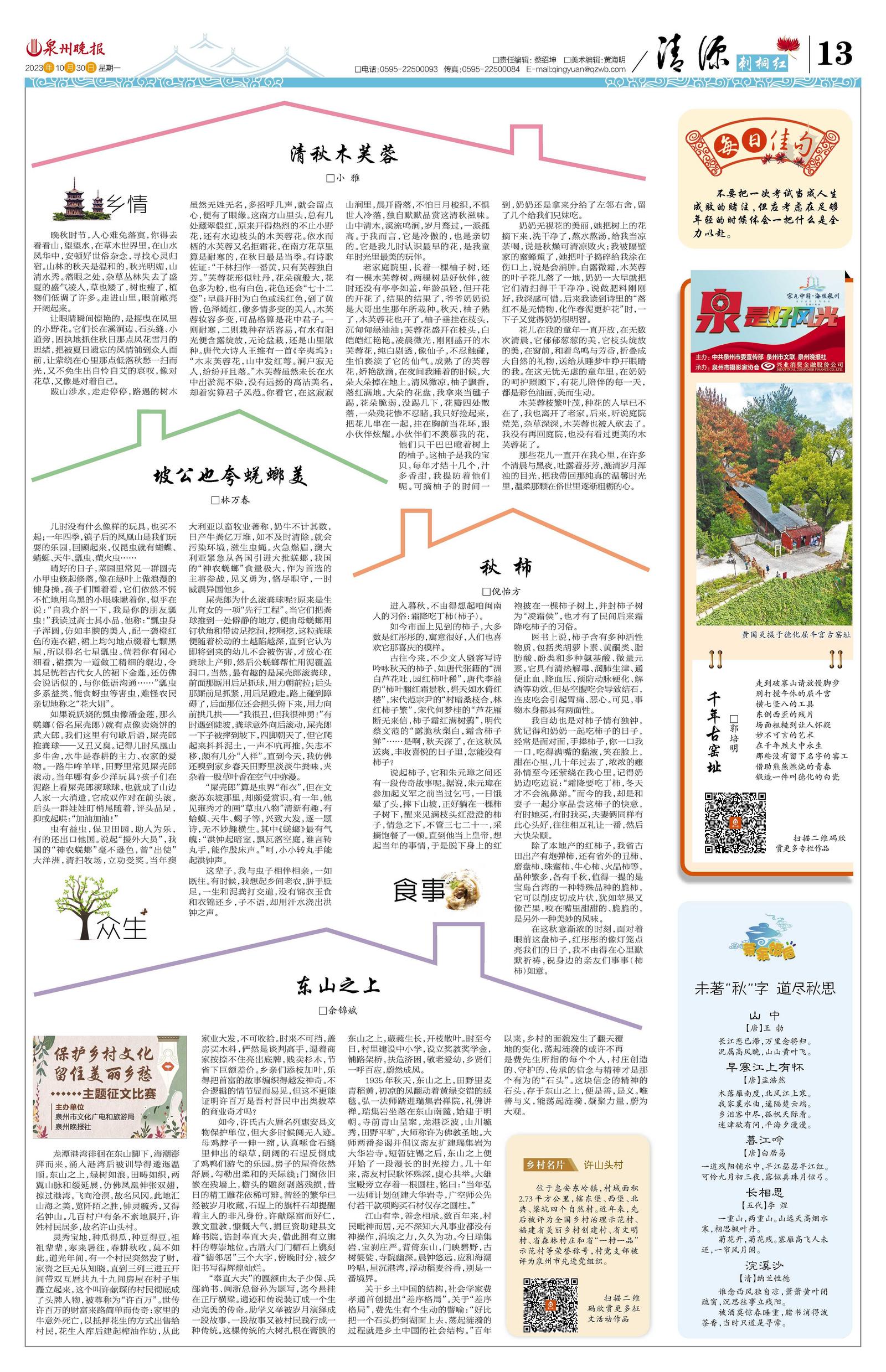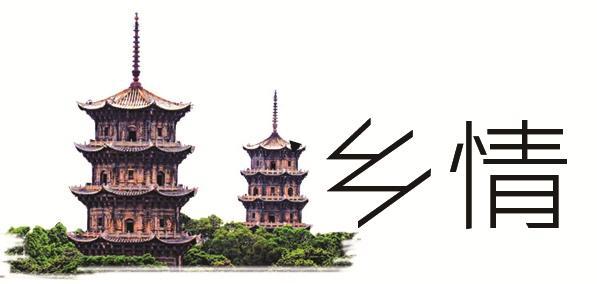晚秋时节,人心难免落寞,你得去看看山,望望水,在草木世界里,在山水风华中,安顿好世俗杂念,寻找心灵归宿。山林的秋天是温和的,秋光明媚,山清水秀。落眼之处,杂草丛林失去了盛夏的盛气凌人,草也矮了,树也瘦了,植物们低调了许多。走进山里,眼前敞亮开阔起来。
让眼睛瞬间惊艳的,是摇曳在风里的小野花。它们长在溪涧边、石头缝、小道旁,固执地抓住秋日那点风花雪月的思绪,把被夏日遗忘的风情铺到众人面前,让萦绕在心里那点低落秋愁一扫而光,又不免生出自怜自艾的哀叹,像对花草,又像是对着自己。
跋山涉水,走走停停,路遇的树木虽然无姓无名,多招呼几声,就会留点心,便有了眼缘。这南方山里头,总有几处藏翠偎红,原来开得热烈的不止小野花,还有水边枝头的木芙蓉花。依水而栖的木芙蓉又名拒霜花,在南方花草里算是耐寒的,在秋日最是当季。有诗歌佐证:“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芙蓉花形似牡丹,花朵碗般大,花色多为粉,也有白色,花色还会“七十二变”:早晨开时为白色或浅红色,到了黄昏,色泽嫣红,像多情多变的美人。木芙蓉妆容多变,可品格算是花中君子。一则耐寒,二则栽种存活容易,有水有阳光便含露绽放,无论盆栽,还是山里散种。唐代大诗人王维有一首《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木芙蓉虽然未长在水中出淤泥不染,没有远扬的高洁美名,却着实算君子风范。你看它,在这寂寂山涧里,晨开昏落,不怕日月梭织,不惧世人冷落,独自默默品赏这清秋滋味。山中清木,溪流鸣涧,岁月骛过,一派孤高。于我而言,它是冷傲的,也是亲切的。它是我儿时认识最早的花,是我童年时光里最美的玩伴。
老家庭院里,长着一棵柚子树,还有一棵木芙蓉树。两棵树是好伙伴,彼时还没有亭亭如盖,年龄虽轻,但开花的开花了,结果的结果了,爷爷奶奶说是大哥出生那年所栽种。秋天,柚子熟了,木芙蓉花也开了。柚子垂挂在枝头,沉甸甸绿油油;芙蓉花盛开在枝头,白皑皑红艳艳。凌晨微光,刚刚盛开的木芙蓉花,纯白剔透,像仙子,不忍触碰,生怕亵渎了它的仙气。成熟了的芙蓉花,娇艳欲滴,在夜间我睡着的时候,大朵大朵掉在地上。清风微凉,柚子飘香,落红满地。大朵的花盘,我拿来当毽子踢,花朵脆弱,没踢几下,花瓣四处散落,一朵残花惨不忍睹。我只好捡起来,把花儿串在一起,挂在胸前当花环,跟小伙伴炫耀。小伙伴们不羡慕我的花,他们只干巴巴瞪着树上的柚子。这柚子是我的宝贝,每年才结十几个,汁多香甜,我提防着他们呢。可摘柚子的时间一到,奶奶还是拿来分给了左邻右舍,留了几个给我们兄妹吃。
奶奶无视花的美丽,她把树上的花摘下来,洗干净了,熬水熬汤,给我当凉茶喝,说是秋燥可清凉败火;我被隔壁家的蜜蜂蜇了,她把叶子捣碎给我涂在伤口上,说是会消肿。白露微霜,木芙蓉的叶子花儿落了一地,奶奶一大早就把它们清扫得干干净净,说做肥料刚刚好,我深感可惜。后来我读到诗里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时,一下子又觉得奶奶很明智。
花儿在我的童年一直开放,在无数次清晨,它郁郁葱葱的美,它枝头绽放的美,在窗前,和着鸟鸣与芳香,折叠成大自然的礼物,送给从睡梦中睁开眼睛的我。在这无忧无虑的童年里,在奶奶的呵护照顾下,有花儿陪伴的每一天,都是彩色油画,美而生动。
木芙蓉枝繁叶茂,种花的人早已不在了,我也离开了老家。后来,听说庭院荒芜,杂草深深,木芙蓉也被人砍去了。我没有再回庭院,也没有看过更美的木芙蓉花了。
那些花儿一直开在我心里,在许多个清晨与黑夜,吐露着芬芳,漉清岁月浑浊的目光,把我带回那纯真的温馨时光里,温柔那颗在俗世里逐渐粗粝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