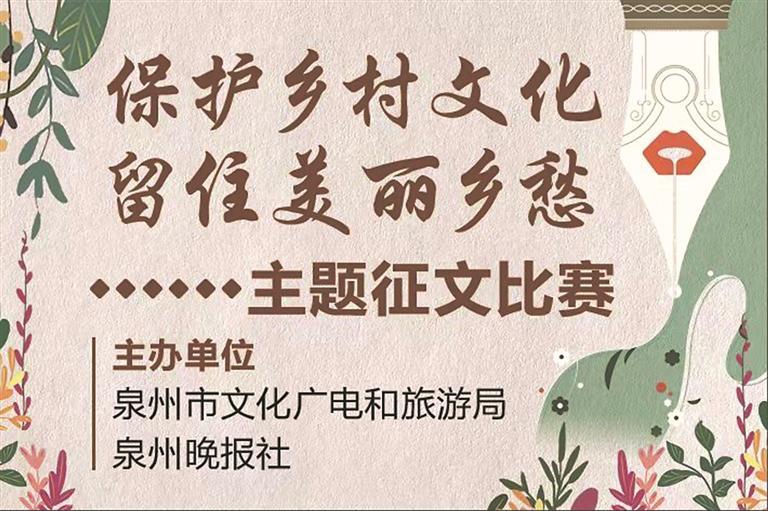在鲤城区新门街西侧,坐落着一座古城门——临漳门,临漳门外,环绕着古城的护城河,笋浯溪。从笋浯溪到笋江这一段,在以前有我的老家——黄甲街。
我的祖父母甚早便迁徙至新门街定居,回黄甲街,要走一段长路。幼时我不知黄甲街的位置,逢人便问:“老家在哪?”祖母说:“新门外,浮桥头。”二姑说:“东西向是街,南北向是路。”我说:“不懂不懂,找不着路。”父亲说:“我带你去。”
父亲的脚踏车载着我,在新门街的石板路上,嘎吱嘎吱、哐当哐当响了一路,遇到一个城门,再奋力往前踩上一阵,接官亭跃入眼帘时,寻觅到左边有条小路,就到了。
一进黄甲街,这头喊着二叔公,奔到另一头就叫起了三婶婆,一家紧挨一家,聚居着亲族的长辈。绕过一厝又一厝,屋舍都是差不多的结构,石栏杆圈着各家的地界,闲暇的傍晚就化作纳凉的坐椅。庭院门口一般都有几个石阶,拾级而上,最先看到的是敞开的大门,白日里一定是不关上的,方便亲友们来访。抬头看,门楣上刻着“汝南衍派”四个字,告示子孙祖脉的源流。厅堂显得庄重肃穆,祖先的牌位和挂像前立着的大方桌,常年摆放着香烛供品。厅堂的角落或偏房里都堆叠着拆零的四方桌和长条凳,招待亲友时搭起来,也能办起祭祀时的流水席。每桌坐八人,挤一挤的话,十二人也坐得下。我多次坐在这样的长条凳上,靠着四方桌,两腿晃悠悠地,吃着宴席,听着族里的长辈们谈古论今。
我们家住新门街,祭祀的是新门街的保护神。祀在闽南话中读“戏”,自然免不了要唱戏。每次祭祀,村里都要搭起戏台子。每家每户都要摆上几桌流水席,村头摆到村尾,亲朋好友们也可一家家吃喝过去,是人声鼎沸的场景。小孩子最爱凑热闹,吃个半饱就要下桌玩,一会儿去戏台边听听戏,一会儿到长辈桌听老人们讲讲故事。男人们吃点饭菜,就迫不及待喝起酒,划起酒拳来。印象中每个泉州男人都懂得划拳,即便平时很缄默的男人,划起拳来就变了一个人,张口就是“五魁首来,六连无,七翘七翘……”手势刚变幻,气势早已就位,声音必须洪亮有力,眼神专注且锐利。划拳似武林高手的对决,个中凶险只有彼此了解,看客们只见“刀光剑影”,看人饮酒才知胜负。这个擂台是闽南人的“战场”,一对一的叫“单挑”,两拨叫阵的叫“分国”,一挑众的高手叫“打通关”,输的赢的都是眉开眼笑,喝醉一个上场一个,直至宴毕,酒尽人散……
后来我年纪渐长,忙于学业,黄甲街渐少踏足。再后来,听闻黄甲街拆迁,原址规划重建,家族长辈迁至泉州城各处居住,如早年般那样相聚再难重现。直至我毕业后工作、结婚、买房,兜兜转转,有一天恍然自己定居之处,竟然离黄甲街原址极近。
千年古街黄甲街现在改建成了笋浯公园,我时常去那里运动跑步。我跑过接官亭,会想起老人们描述古时此处迎接官员的盛况,想起接官亭是亭也是庙,后来不接官了就只做庙;想起黄甲古地藏于此处,黄甲大元帅宫也迁入此地,会在心里默默跟他打个招呼然后继续往前。我跑到石笋古渡,断了的古浮桥仍在见证笋江的潮起潮落,而“笋江月色”的十六轮皓月却再也无法重现。我跑到被圈起来的树林前,它们挂着“原状保护区”的牌子,看到一些身姿妖娆的龙眼树,会想象当年每次黄甲街的龙眼林丰收时,亲戚们给我们大袋大袋送去的龙眼中,有没有哪些,是这些树结过的果子。我跑过一圈又一圈,笋浯溪接纳了城内大大小小壕沟流入的水,看起来却那么安静,安静得好似不在流动。但它汇入笋江晋江的接口处,水流却总显得那么急迫,如同我幼时每次进黄甲街的步履。
笋浯公园有处碑林,碑刻百家姓中古老姓氏与其堂号,碑阵设计成一个篆体的“和”字,穿行其中如同穿行于姓氏历史中。我在“周”姓的碑刻前久久驻足,看“汝南衍派”四个字,是与幼时自己看着大门门楣那刻,一样的血脉呼唤。童年时的我只知蹦蹦跳跳,天真烂漫,成年之后,才在无数次的回忆里,懂得自己的遗憾——是与宗亲共度的时光不再得以延长,是与故地的接触只能在梦中重现。宗族就是那条长长的母亲河,我们每个人都是水。民俗文化和节庆活动就是那些宽宽窄窄的河道,聚拢每一滴水汇入母亲河。
夏天的傍晚,我跑过某一棵大树时,会突然有巨大的蝉鸣声唱响,听起来就像:“黄甲街啊。”黄甲街其实仍在那里,在护城河和母亲河之间,默默守望着每一个子孙。
乡村名片
浮桥社区
浮桥社区历史悠久,名人辈出。主要名胜古迹有笋江月色、石笋桥、接官亭、宋代三座古石桥等,与南音、十音以及民俗文化车鼓阵、舞龙等,形成社区独特传统文化魅力。社区内黄甲街位于临漳门外晋江北岸,是古早的港口街市,商业曾称雄一时,四方商贾云集,原址现已改建成石笋公园和笋浯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