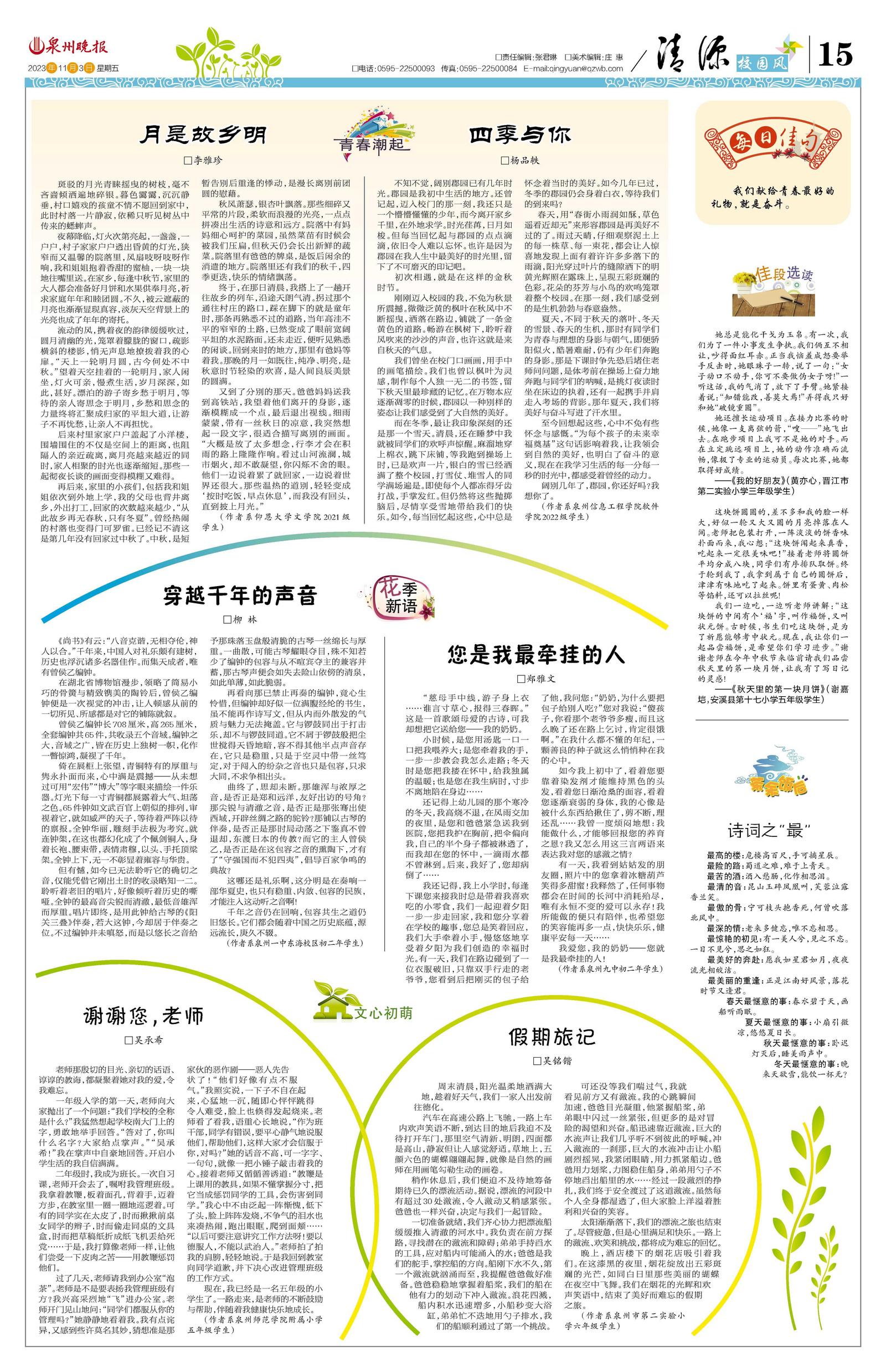□柳 林
《尚书》有云:“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合。”千年来,中国人对礼乐颇有建树,历史也浮沉诸多名器佳作。而集天成者,唯有曾侯乙编钟。
在湖北省博物馆漫步,领略了简易小巧的骨簧与精致镌美的陶铃后,曾侯乙编钟便是一次视觉的冲击,让人顿感从前的一切所见、所感都是对它的铺陈就叙。
曾侯乙编钟长708厘米,高265厘米,全套编钟共65件,共收录五个音域。编钟之大,音域之广,皆在历史上独树一帜,化作一瞥惊鸿,凝视了千年。
倚在展柜上张望,青铜特有的厚重与隽永扑面而来,心中满是震撼——从未想过可用“宏伟”“博大”等字眼来描绘一件乐器。灯光下每一寸青铜都展露着大气、坦荡之色。65件钟如文武百官上朝似的排列,审视着它,就如威严的天子,等待着严阵以待的禀报。全钟华丽,雕刻手法极为考究。就连钟架,在这也都幻化成了个佩剑铜人,身着长袍、腰束带,表情肃穆,以头、手托顶梁架。全钟上下,无一不彰显着雍容与华贵。
但有憾,如今已无法聆听它的确切之音,仅能凭借它刚出土时的收录略知一二。聆听着老旧的唱片,好像倾听着历史的嘶哑。全钟的最高音尖锐而清澈,最低音雄浑而厚重。唱片即终,是用此钟给古琴的《阳关三叠》伴奏,若大这钟,今却居于伴奏之位。不过编钟并未嗔怒,而是以悠长之音给予那珠落玉盘般清脆的古琴一丝绵长与厚重。一曲散,可能古琴耀眼夺目,殊不知若少了编钟的包容与从不喧宾夺主的兼容并蓄,那古琴声便会如失去险山依傍的清泉,如此单薄,如此脆弱。
再看向那已禁止再奏的编钟,竟心生怜惜,但编钟却好似一位满腹经纶的书生,虽不能再作诗写文,但从内而外散发的气质与魅力无法掩盖。它与锣鼓同出于打击乐,却不与锣鼓同道。它不屑于锣鼓般把尘世搅得天昏地暗,容不得其他半点声音存在,它只是稳重,只是于空灵中带一丝笃定,对于闯入的纷杂之音也只是包容,只求大同,不求争相出头。
曲终了,思却未断。那雄浑与浓厚之音,是否正是郑和远洋,友好出访的号角?那尖锐与清澈之音,是否正是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的驼铃?那铺以古琴的伴奏,是否正是那时局动荡之下鉴真不曾退却,东渡日本的传教?而它的主人曾侯乙,是否正是在这包容之音的熏陶下,才有了“守强国而不犯四夷”,倡导百家争鸣的典故?
这哪还是礼乐啊,这分明是在奏响一部华夏史,也只有稳重、内敛、包容的民族,才能注入这动听之音啊!
千年之音仍在回响,包容共生之道仍旧悠长。它们都会随着中国之历史底蕴,源远流长,庚久不辍。
(作者系泉州一中东海校区初二年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