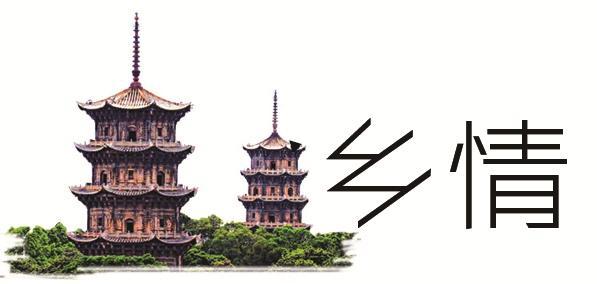“木密集旃檀,青莲诸雨香。”这句诗道尽了苦檀香的香气,据说苦檀香“热之能夺众香”,可见其香味之独特。
采苦檀香是讲究季节的,通常是白露过后采,这时的苦檀香香味最醇厚。苦檀香一般作为主香制作合香,乡人却一向单烧苦檀香,想来粗俗之人亦有奢侈之趣。
家乡有个依悬崖而建的古村落,悬崖之上尽是苍苍古木,其中便有一株苦檀树,这苦檀树依附峭壁而长,其果实落于石罅间,很难成活,所以虽经百年光阴,却也只是孤独的一株。村人每年采集它的叶子,晒干了,请两三个伙计夜以继日舂成香粉,再装在瓮子里备用。苦檀树下有小庙,有老者每天在香模上洒出几道回环的香迹,点燃了,庙里庙外是香的,整座村庄也是香的。收成后的秋日里,上了年纪的老人每天晨昏之时便聚在小庙里,就着苦檀香的香气聊些种子与收成的事儿。
后来下了一场暴雨,悬崖上的房屋有坍塌的危险,村人便商议集体搬回大村。那株苦檀树长得太高了,已经无法随乡人一起搬迁,它理所当然成了村庄的守护者,村人也没有忘记它,几乎每个月都有老人回去看看那些房子,也看看那株苦檀树。
搬回来的大村里有大庙,庙里终年点着苦檀香。庙后樟公岭上常有往来种作的农人,闻着这绵延不绝的清香,他们边挥舞着锄头边满足地说:“哎呀,真是近地烧香远地香。”
守庙的是一对老夫妻,他们还负责准备这一年又一年的苦檀香。于是他们每年都会到山那边的悬崖上去“采香”,带上芼担、麻绳、钩杆,爬一段极陡的石岭,到了那树下,站在峭壁上,用钩杆钩住那苦檀树的小枝,那枝脆着呢,一钩就下来了。夫妻俩采足了枝叶,捆成两担,一前一后挑着走五六里山路回家。到家后,把叶子晒干了磨成香粉,枝干劈成小枝一捆捆放着。刚刚砍下的苦檀枝也会有植物的腥气,须放置一段时间。等民俗的日子一到,守庙人把苦檀香枝点燃了放在香盘里,两个穿着汉服的人把香盘吊在脖子上,随大队人马走到山顶的庙里去,后面有人提着一布袋的苦檀香枝等着续香,凡“奉香人”走过的路都带着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
这对老夫妻八十岁后就不再去悬崖边“采香”了,这株铜盆大的苦檀树也在一次森林火灾中化为香烬。
父亲说,我家的瓦窖边从前也种着一株苦檀树,那是我的祖爷爷种下的,经过几代人的照顾,那树的直径有粿桶那么大了。到了爷爷这一代,爷爷每年都须爬十一级的木梯才能采到苦檀树的叶子。采回后,爷爷把苦檀香叶倒在门埕外的晒米石上晒干了,放入木臼中捣三四百杵,再倒入石磨里碨成香粉,收在陶罐里,那就是我家一年的香料了。逢年过节,爷爷从陶罐里抓一把苦檀香粉,在石香炉上洒出回环的香迹,再从大灶里夹一块烧得通红的木炭放那香迹上,那苦檀香就一点点地燃烧,在老房子里氤氲出袅袅的香气。从祖爷爷开始,这株苦檀树的叶子在我家的石香炉里燃烧了近两百年,以致我家神龛里的泥菩萨都被熏出了苦檀香的味道。
到了1958年,生产队要平整土地,爷爷只好把那株苦檀树砍了,砍的前一夜,爷爷在这株苦檀树前坐了三个小时,抽了十几袋烟才下手。那砍下来的苦檀树,一个刣木屐的手艺人花七元钱买走了。
用苦檀树刣出来的木屐,我没有见过,大约以后也是见不到的。
村里还有一位极喜苦檀香的老女人,她的屋子周围种着五六株碗口大的苦檀树。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上了年纪了,她平日里极少出门,只是每日在自家天地里读些经书。她家的香模里终日点着苦檀香,她就在这微凉的香气中喝喝茶、写写字,有时也来一位年纪相仿的老妇,两人便坐着心平气和地聊半日闲天。
这个老女人不种菜,倒是种了四五株山栀子,那栀子七月里开极白的花,栀子花的清香与苦檀香混杂在一起,清远得让人无法言说。她家门上贴的对联也与别家的不一样,“明窗延静书,默坐消尘缘”,娟秀的字迹,应是她自己抄写的吧。我上班路上每每从她家门前经过,屡次想敲门拜访,终于觉得此举亦可省去,但每次走到这里,我都会停下脚步,看看墙角那些栀子花的长势,想象屋内那位正在读书或写字,香灰堆积,炉薰一室。
等老了的时候,也学她焚香读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