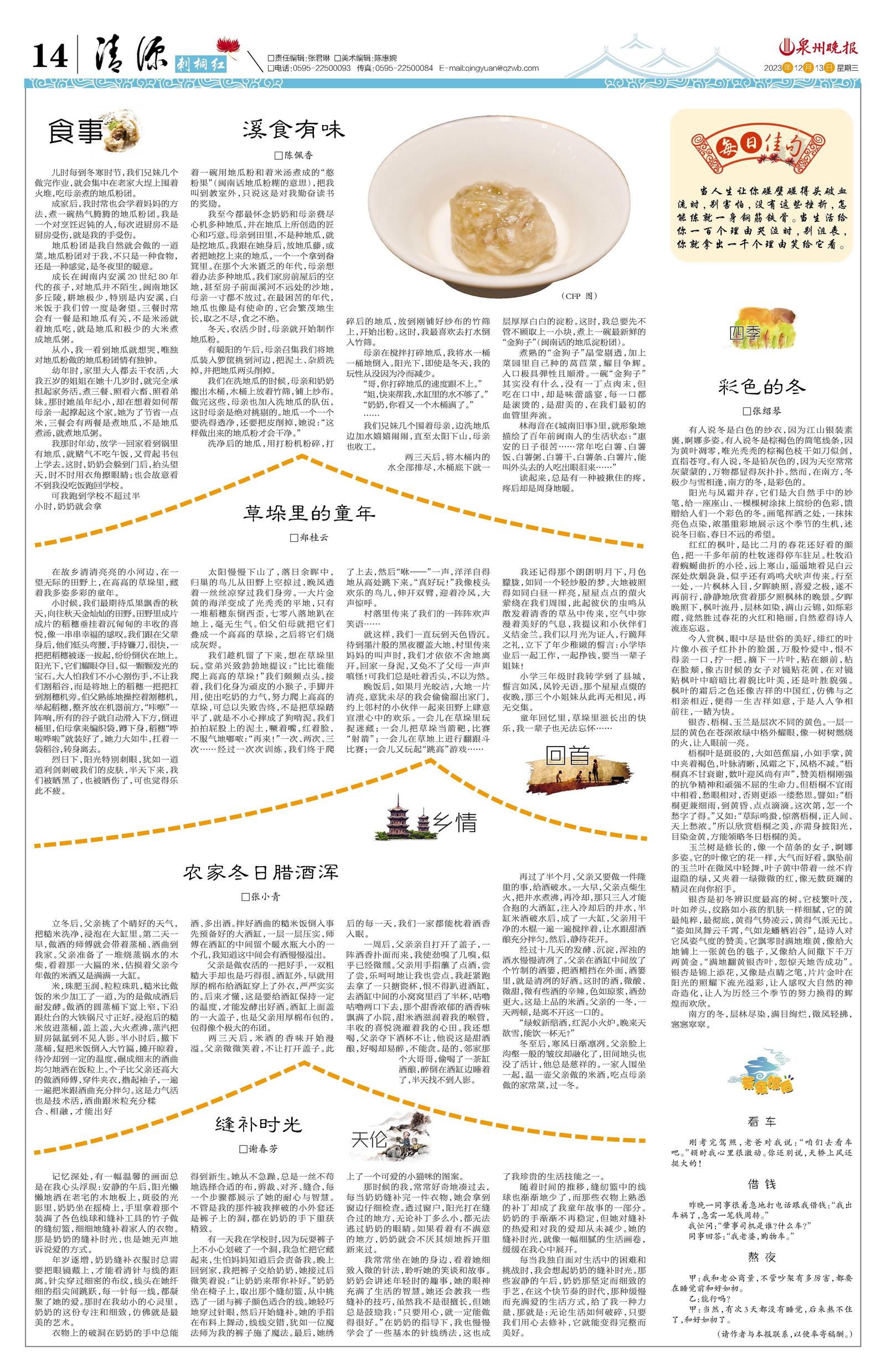□陈佩香
儿时每到冬寒时节,我们兄妹几个做完作业,就会集中在老家大埕上围着火堆,吃母亲煮的地瓜粉团。
成家后,我时常也会学着妈妈的方法,煮一碗热气腾腾的地瓜粉团。我是一个对烹饪迟钝的人,每次进厨房不是厨房受伤,就是我的手受伤。
地瓜粉团是我自然就会做的一道菜。地瓜粉团对于我,不只是一种食物,还是一种感觉,是冬夜里的暖意。
成长在闽南内安溪20世纪80年代的孩子,对地瓜并不陌生。闽南地区多丘陵,耕地极少,特别是内安溪,白米饭于我们曾一度是奢望。三餐时常会有一餐是和地瓜有关,不是米汤就着地瓜吃,就是地瓜和极少的大米煮成地瓜粥。
从小,我一看到地瓜就想哭,唯独对地瓜粉做的地瓜粉团情有独钟。
幼年时,家里大人都去干农活,大我五岁的姐姐在她十几岁时,就完全承担起家务活。煮三餐、照看六畜、照看弟妹。那时她虽年纪小,却在想着如何帮母亲一起撑起这个家。她为了节省一点米,三餐会有两餐是煮地瓜,不是地瓜煮汤,就煮地瓜粥。
我那时年幼,放学一回家看到锅里有地瓜,就赌气不吃午饭,又背起书包上学去。这时,奶奶会躲到门后,抬头望天,时不时用衣角擦眼睛;也会故意看不到我没吃饭跑回学校。
可我跑到学校不超过半小时,奶奶就会拿着一碗用地瓜粉和着米汤煮成的“憨粉果”(闽南话地瓜粉糊的意思),把我叫到教室外,只说这是对我勤奋读书的奖励。
我至今都最怀念奶奶和母亲费尽心机多种地瓜,并在地瓜上所创造的匠心和巧意。母亲到田里,不是种地瓜,就是挖地瓜。我跟在她身后,放地瓜藤,或者把她挖上来的地瓜,一个一个拿到畚箕里。在那个大米匮乏的年代,母亲想着办法多种地瓜。我们家房前屋后的空地,甚至房子前面溪河不远处的沙地,母亲一寸都不放过。在最困苦的年代,地瓜也像是有使命的,它会繁茂地生长,取之不尽,食之不绝。
冬天,农活少时,母亲就开始制作地瓜粉。
有暖阳的午后,母亲召集我们将地瓜装入箩筐挑到河边,把泥土、杂质洗掉,并把地瓜两头削掉。
我们在洗地瓜的时候,母亲和奶奶搬出木桶,木桶上放着竹筛,铺上纱布。做完这些,母亲也加入洗地瓜的队伍,这时母亲是绝对挑剔的。地瓜一个一个要洗得透净,还要把皮削掉,她说:“这样做出来的地瓜粉才会干净。”
洗净后的地瓜,用打粉机粉碎,打碎后的地瓜,放到刚铺好纱布的竹筛上,开始出粉。这时,我最喜欢去打水倒入竹筛。
母亲在搅拌打碎地瓜,我将水一桶一桶地倒入。阳光下,即使是冬天,我的玩性从没因为冷而减少。
“哥,你打碎地瓜的速度跟不上。”
“姐,快来帮我,水缸里的水不够了。”
“奶奶,你看又一个木桶满了。”
……
我们兄妹几个围着母亲,边洗地瓜边加水嬉嬉闹闹,直至太阳下山,母亲也收工。
两三天后,将木桶内的水全部排尽,木桶底下就一层厚厚白白的淀粉。这时,我总要先不管不顾取上一小块,煮上一碗最新鲜的“金狗子”(闽南话的地瓜淀粉团)。
煮熟的“金狗子”晶莹剔透,加上菜园里自己种的莴苣菜,耀目争辉。入口极具弹性且顺滑。一碗“金狗子”其实没有什么,没有一丁点肉末,但吃在口中,却是味蕾盛宴,每一口都是滚烫的,是甜美的,在我们最初的血管里奔流。
林海音在《城南旧事》里,就形象地描绘了百年前闽南人的生活状态:“惠安的日子很苦……常年吃白薯、白薯饭、白薯粥、白薯干、白薯条、白薯片,能叫外头去的人吃出眼泪来……”
读起来,总是有一种被揪住的疼,疼后却是周身地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