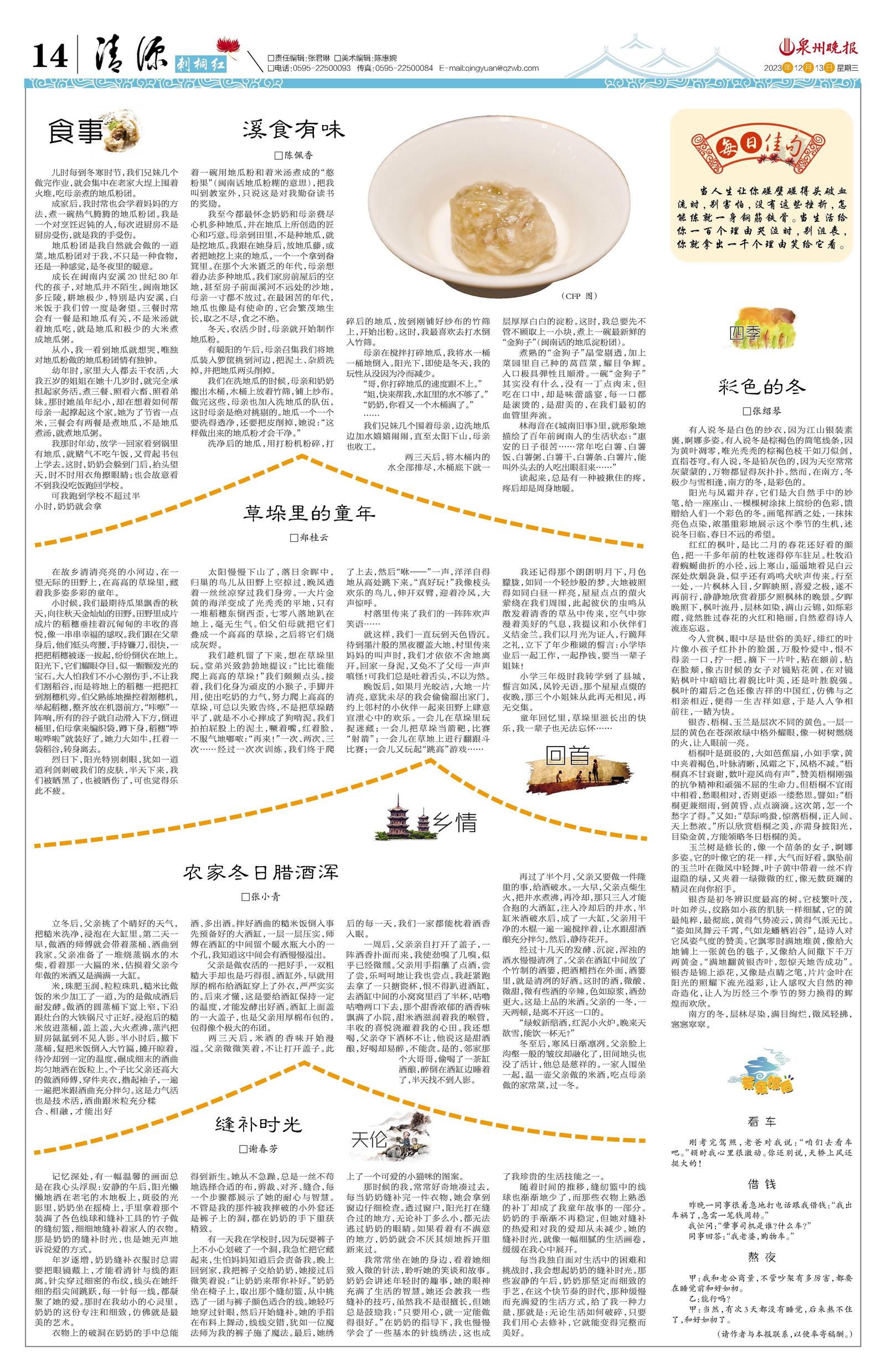□张小青
立冬后,父亲挑了个晴好的天气,把糙米洗净,浸泡在大缸里。第二天一早,做酒的师傅就会带着蒸桶、酒曲到我家。父亲准备了一堆烧蒸锅水的木柴,看着那一大匾的米,估摸着父亲今年做的米酒又是满满一大缸。
米,珠肥玉润、粒粒珠玑,糙米比做饭的米少加工了一道,为的是做成酒后耐发酵。做酒的圆蒸桶下宽上窄,下沿跟灶台的大铁锅尺寸正好。浸泡后的糙米放进蒸桶,盖上盖,大火煮沸,蒸汽把厨房氤氲到不见人影。半小时后,撤下蒸桶,复把米饭倒入大竹匾,摊开晾着,待冷却到一定的温度,碾成细末的酒曲均匀地洒在饭粒上。个子比父亲还高大的做酒师傅,穿件夹衣,撸起袖子,一遍一遍把米跟酒曲充分拌匀。这是力气活也是技术活,酒曲跟米粒充分糅合、相融,才能出好酒、多出酒。拌好酒曲的糙米饭倒入事先预备好的大酒缸,一层一层压实,师傅在酒缸的中间留个暖水瓶大小的一个孔,我知道这中间会有酒慢慢溢出。
父亲是做农活的一把好手,一双粗糙大手却也是巧得很。酒缸外,早就用厚的棉布给酒缸穿上了外衣,严严实实的。后来才懂,这是要给酒缸保持一定的温度,才能发酵出好酒。酒缸上面盖的一大盖子,也是父亲用厚棉布包的,包得像个极大的布团。
两三天后,米酒的香味开始漫溢。父亲微微笑着,不让打开盖子。此后的每一天,我们一家都能枕着酒香入眠。
一周后,父亲亲自打开了盖子,一阵酒香扑面而来,我使劲嗅了几嗅,似乎已经微醺。父亲用手指蘸了点酒,尝了尝,乐呵呵地让我也尝点。我赶紧跑去拿了一只搪瓷杯,恨不得趴进酒缸,去酒缸中间的小窝窝里舀了半杯,咕噜咕噜两口下去,那个甜香浓郁的酒香味飘满了小院,甜米酒滋润着我的喉管,丰收的喜悦浇灌着我的心田。我还想喝,父亲夺下酒杯不让,他说这是甜酒酿,好喝却易醉,不能贪。是的,邻家那个大哥哥,偷喝了一茶缸酒酿,醉倒在酒缸边睡着了,半天找不到人影。
再过了半个月,父亲又要做一件隆重的事,给酒破水。一大早,父亲点柴生火,把井水煮沸,再冷却,那只三人才能合抱的大酒缸,注入冷却后的井水,半缸米酒破水后,成了一大缸,父亲用干净的木棍一遍一遍搅拌着,让水跟甜酒酿充分拌匀。然后,静待花开。
经过十几天的发酵、沉淀,浑浊的酒水慢慢清冽了。父亲在酒缸中间放了个竹制的酒篓,把酒糟挡在外面,酒篓里,就是清冽的好酒。这时的酒,微酸、微甜,微有些酒的辛辣,色如琼浆,酒劲更大。这是上品的米酒。父亲的一冬,一天两顿,是离不开这一口的。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冬至后,寒风日渐凛冽。父亲脸上沟壑一般的皱纹却融化了,田间地头也没了活计,他总是慈祥的。一家人围坐一起,温一壶父亲做的米酒,吃点母亲做的家常菜,过一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