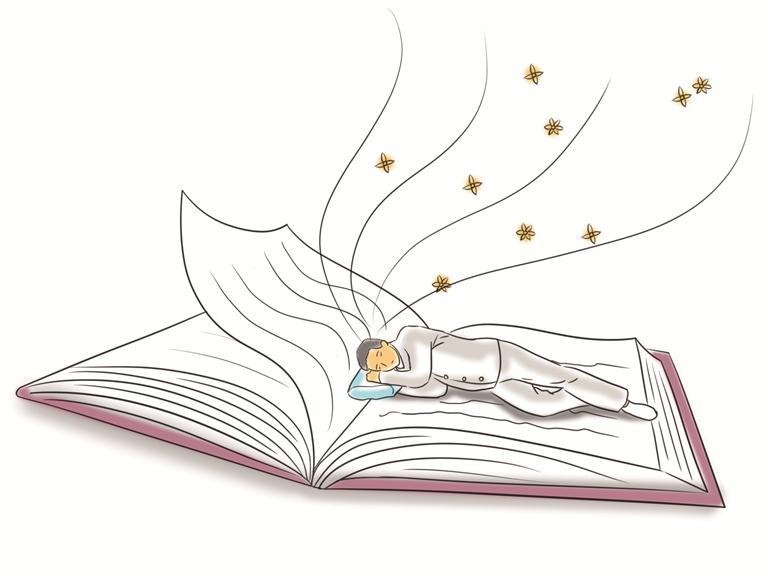“体倦尚凭书引睡,心安不假酒攻愁。”这是晚年的陆游写下的诗句,也极有可能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实不相瞒,如今的我便也是如放翁先生一般,“引睡书横犹在架”,在缓缓流淌的时光里,往往是读着书入清梦。
小时候顽皮,逢了夏日酷热沉闷,蝉声聒噪,大人们午睡,我却偷偷爬至树上,在院子里那棵大梧桐树上读书。放一张纸片当坐垫,骑在树杈上,还煞有介事地将自己与身后靠着的树干用布条捆在一起,这样感觉安全又惬意。读一本简单的书,不过是新发的或已经读过好几遍的语文课本罢了,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沉浸在散发着油墨味道的文字里,能忘记一切,偏偏不困,捆绑显得多余。清秋如约而至,我必是一有时间就钻进屋后的杨树林,踩着厚厚的一层叶子,找最安静的角落,读书。彼时,有暖暖的午后阳光贴在身上。读书间隙,身子向后一躺,压得枯树叶嘎吱嘎吱响,望一会儿碎块拼成的浅蓝色的天,听一听秋风从另一个村子赶来的呼呼脚步声,想一些不着边际的小心事,我的童年清新而诗意。
三十年倏忽而去,此时我在冬日暖阳下读肖复兴先生的一本书《我们的上面是天空》,读到其中一篇,是写给八百余年前陆放翁先生的一封信。今人与古人对话,令人感到奇妙又恍惚,我竟有些昏昏欲睡了。想着两位老人隔空推心置腹地闲谈,惺惺惜惺惺,作为旁观者只有仰慕的份儿,只有不敢打扰的份儿,放下书,倚着公园里的木椅,我一脸微笑地睡着了。小睡醒来,手捧书卷,听沙沙林叶响,格外满足。
想起昨晚临睡前,趴在被窝里读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一书,读到眼皮打架,仍不肯睡,最后还是抵挡不过劳累和瞌睡虫的双面攻击,败下阵来。以书引睡,最好不过。捧书而睡,枕书而眠,皆安逸。说不上来的感觉,大约是一种富足感和安全感,或者是自由出入到另外世界的漫游感。醒来发现书犹在,人犹在,世界平和,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书无声,却使人明理,教人深思。想王维在终南山上,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悠闲、从容、淡定真叫人艳羡。这与其佛学思想有关,更与其写诗、画画、读书脱不开干系。我辈虽不能如王维如陆游,但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把日子过得尽量从容、舒缓一些,读书应是最佳选择。
读放翁先生的“引睡书横犹在架,围棋客散但空枰”,不觉又想起丰子恺先生所作的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那清幽,那清雅,那清静,妙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