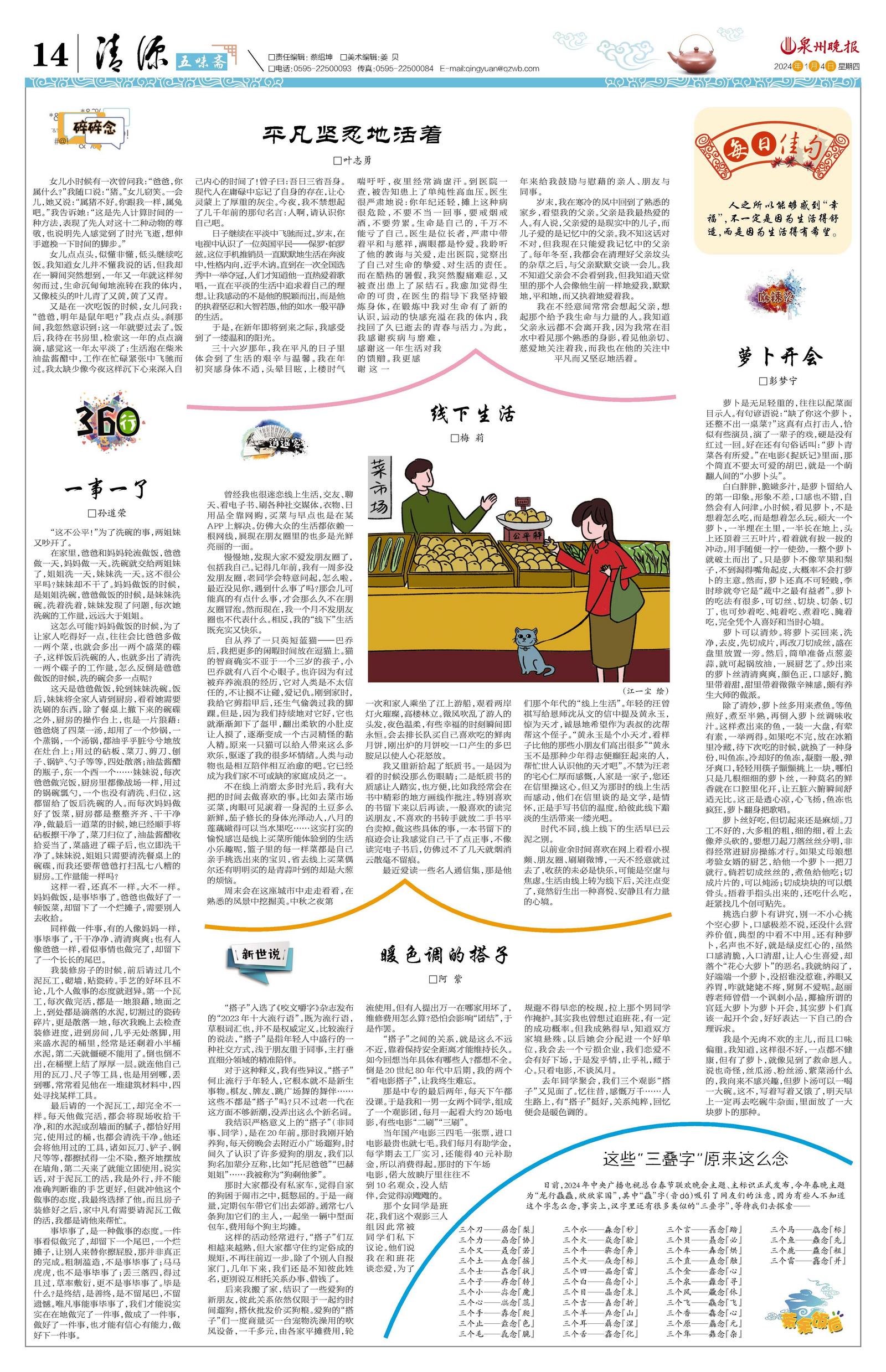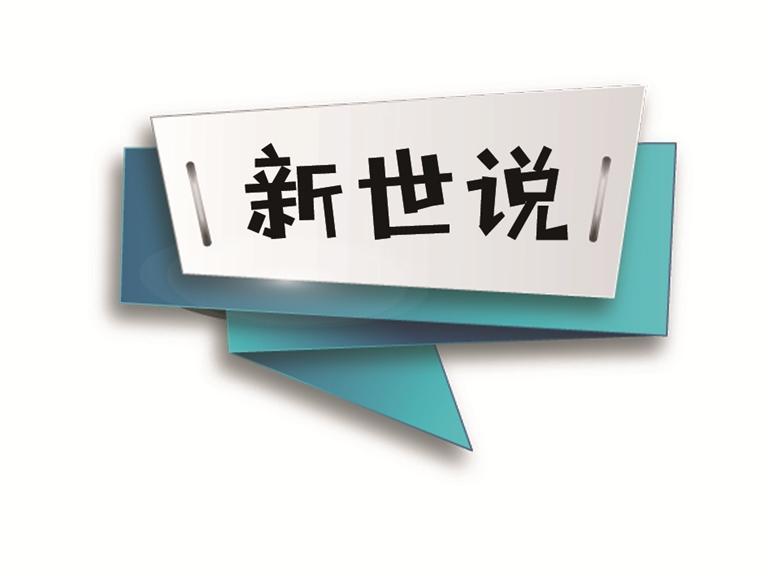“搭子”入选了《咬文嚼字》杂志发布的“2023年十大流行语”。既为流行语,草根词汇也,并不是权威定义。比较流行的说法,“搭子”是指年轻人中盛行的一种社交方式,浅于朋友重于同事,主打垂直细分领域的精准陪伴。
对于这种释义,我有些异议。“搭子”何止流行于年轻人,它根本就不是新生事物。棋友、牌友、跳广场舞的舞伴……这些不都是“搭子”吗?只不过老一代在这方面不够新潮,没弄出这么个新名词。
我结识严格意义上的“搭子”(非同事、同学),是在20年前。那时我刚开始养狗,每天傍晚会去附近小广场遛狗。时间久了认识了许多爱狗的朋友,我们以狗名加辈分互称,比如“托尼爸爸”“巴赫姐姐”……我被称为“狗剩他爹”。
那时大家都没有私家车,觉得自家的狗困于闹市之中,挺憋屈的。于是一商量,定期包车带它们出去郊游。通常七八条狗加它们的主人,一起坐一辆中型面包车,费用每个狗主均摊。
这样的活动经常进行,“搭子”们互相越来越熟,但大家都守住约定俗成的规矩,不再往前迈一步。除了个别人自报家门,几年下来,我们还是不知彼此姓名,更别说互相托关系办事、借钱了。
后来我搬了家,结识了一些爱狗的新朋友,彼此关系依然仅限于一起约时间遛狗,搭伙批发价买狗粮。爱狗的“搭子”们一度商量买一台宠物洗澡用的吹风设备,一千多元,由各家平摊费用,轮流使用。但有人提出万一在哪家用坏了,维修费用怎么算?恐怕会影响“团结”,于是作罢。
“搭子”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不远不近,靠着保持安全距离才能维持长久。如今回想当年具体有哪些人?都想不全。倒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的两个“看电影搭子”,让我终生难忘。
那是中专的最后两年,每天下午都没课。于是我和一男一女两个同学,组成了一个观影团,每月一起看大约20场电影,有些电影“二刷”“三刷”。
当年国产电影三四毛一张票,进口电影最贵也就七毛。我们每月有助学金,每学期去工厂实习,还能得40元补助金,所以消费得起。那时的下午场电影,偌大放映厅里往往不到10名观众,没人结伴,会觉得凉飕飕的。
那个女同学是班花,我们这个观影三人组因此常被同学们私下议论。他们说我在和班花谈恋爱,为了规避不得早恋的校规,拉上那个男同学作掩护。其实我也曾想过追班花,有一定的成功概率。但我成熟得早,知道双方家境悬殊。以后她会分配进一个好单位,我会去一个亏损企业,我们恋爱不会有好下场,于是发乎情,止乎礼,藏于心。只看电影,不谈风月。
去年同学聚会,我们三个观影“搭子”又见面了。忆往昔,感慨万千……人生路上,有“搭子”挺好,关系纯粹,回忆便会是暖色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