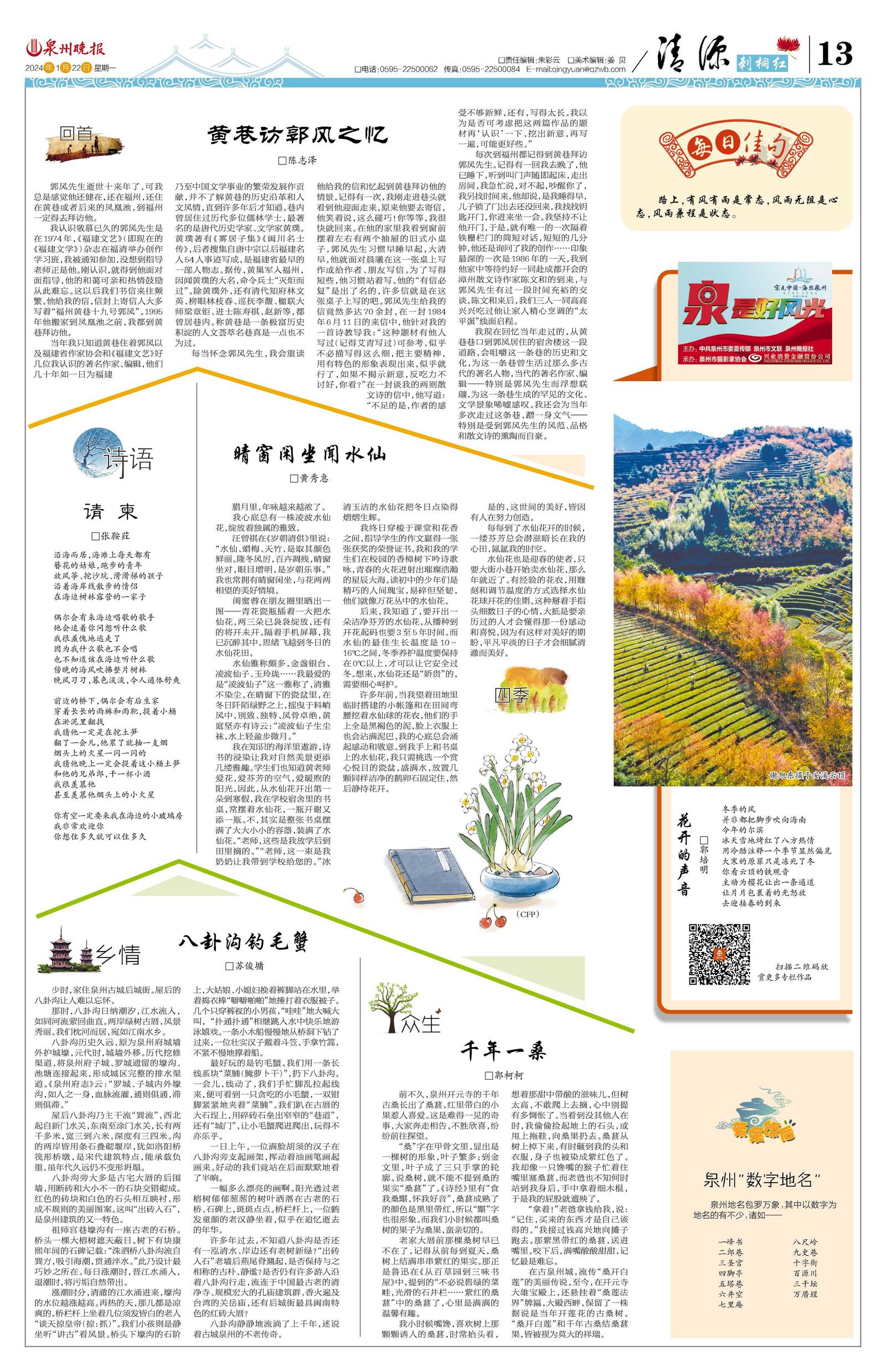郭风先生逝世十来年了,可我总是感觉他还健在,还在福州,还住在黄巷或者后来的凤凰池,到福州一定得去拜访他。
我认识敬慕已久的郭风先生是在1974年,《福建文艺》(即现在的《福建文学》)杂志在福清举办创作学习班,我被通知参加,没想到指导老师正是他。刚认识,就得到他面对面指导,他的和蔼可亲和热情鼓励从此难忘。这以后我们书信来往频繁。他给我的信,信封上寄信人大多写着“福州黄巷十九号郭风”。1995年他搬家到凤凰池之前,我都到黄巷拜访他。
当年我只知道黄巷住着郭风以及福建省作家协会和《福建文艺》好几位我认识的著名作家、编辑,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为福建乃至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作贡献,并不了解黄巷的历史沿革和人文风情,直到许多年后才知道,巷内曾居住过历代多位儒林学士,最著名的是唐代历史学家、文学家黄璞。黄璞著有《雾居子集》《闽川名士传》,后者搜集自唐中宗以后福建名人54人事迹写成,是福建省最早的一部人物志。据传,黄巢军入福州,因闻黄璞的大名,命令兵士“灭炬而过”。除黄璞外,还有清代知府林文英、榜眼林枝春、巡抚李馥、楹联大师梁章钜、进士陈寿祺、赵新等,都曾居巷内。称黄巷是一条极富历史积淀的人文荟萃名巷真是一点也不为过。
每当怀念郭风先生,我会重读他给我的信和忆起到黄巷拜访他的情景。记得有一次,我刚走进巷头就看到他迎面走来,原来他要去寄信,他笑着说,这么碰巧!你等等,我很快就回来。在他的家里我看到窗前摆着左右有两个抽屉的旧式小桌子,郭风先生习惯早睡早起,大清早,他就面对晨曦在这一张桌上写作或给作者、朋友写信。为了写得短些,他习惯站着写。他的“有信必复”是出了名的,许多信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写的吧。郭风先生给我的信竟然多达70余封,在一封1984年6月11日的来信中,他针对我的一首诗教导我:“这种题材有他人写过(记得艾青写过)可参考,似乎不必描写得这么细,把主要精神,用有特色的形象表现出来,似乎就行了,如果不揭示新意,反吃力不讨好,你看?”在一封谈我的两则散文诗的信中,他写道:“不足的是,作者的感受不够新鲜,还有,写得太长。我以为是否可考虑把这两篇作品的题材再‘认识’一下,挖出新意,再写一遍,可能更好些。”
每次到福州都记得到黄巷拜访郭风先生。记得有一回我去晚了,他已睡下,听到叫门声随即起床,走出房间,我急忙说,对不起,吵醒你了,我另找时间来。他却说,是我睡得早,儿子锁了门出去还没回来,我找找钥匙开门,你进来坐一会。我坚持不让他开门,于是,就有唯一的一次隔着铁栅栏门的简短对话,短短的几分钟,他还是询问了我的创作……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86年的一天,我到他家中等待约好一同赴成都开会的漳州散文诗作家陈文和的到来,与郭风先生有过一段时间充裕的交谈,陈文和来后,我们三人一同高高兴兴吃过他让家人精心烹调的“太平蛋”线面启程。
我现在回忆当年走过的,从黄巷巷口到郭风居住的宿舍楼这一段道路,会咀嚼这一条巷的历史和文化,为这一条巷曾生活过那么多古代的著名人物,当代的著名作家、编辑——特别是郭风先生而浮想联翩,为这一条巷生成的罕见的文化、文学景象唏嘘感叹。我还会为当年多次走过这条巷,蹭一身文气——特别是受到郭风先生的风范、品格和散文诗的熏陶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