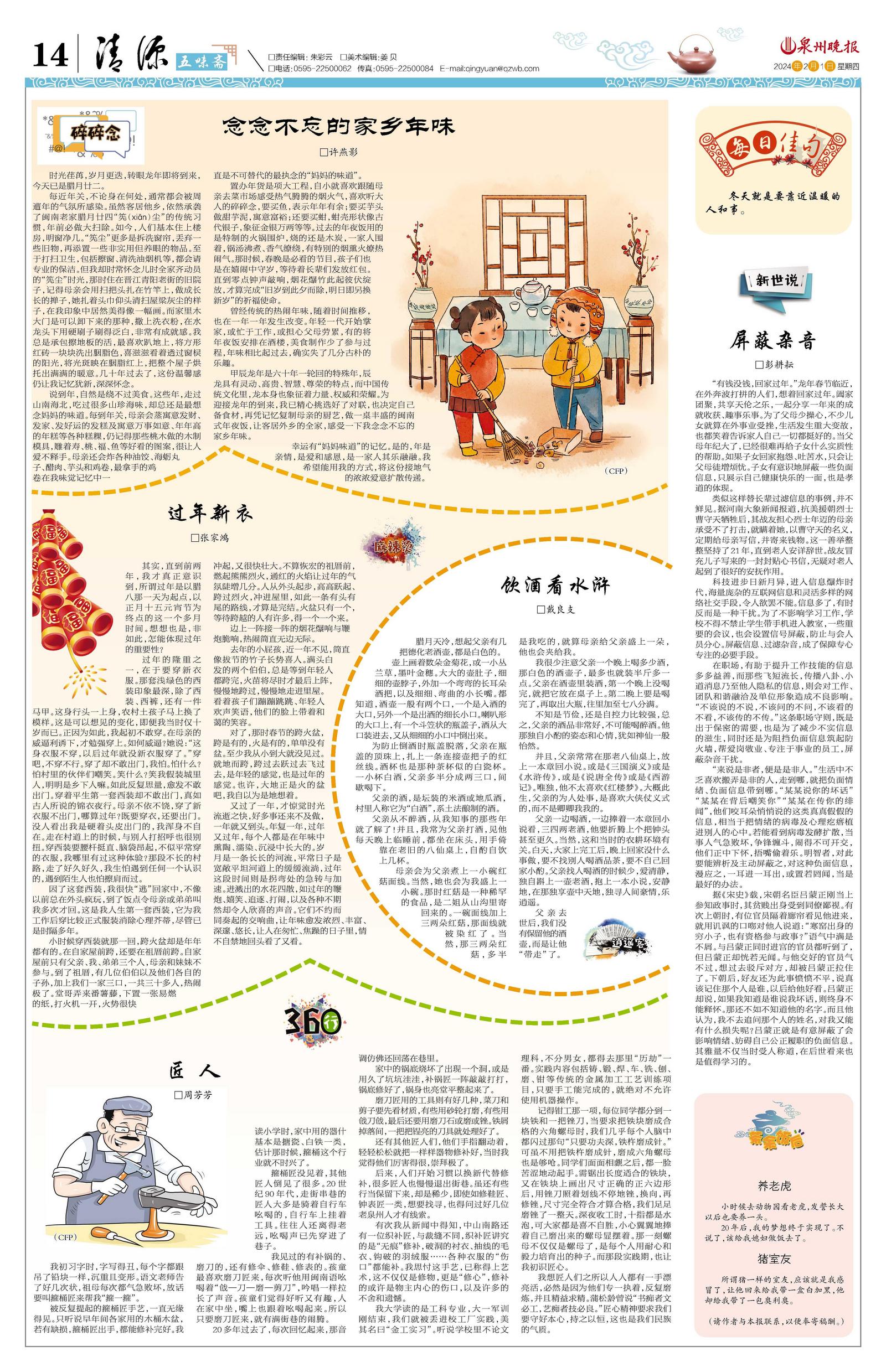其实,直到前两年,我才真正意识到,所谓过年是以腊八那一天为起点,以正月十五元宵节为终点的这一个多月时间。想想也是,非如此,怎能体现过年的重要性?
过年的隆重之一,在于要穿新衣服。那套浅绿色的西装印象最深,除了西装、西裤,还有一件马甲。这身行头一上身,农村土孩子马上换了模样。这是可以想见的变化,即便我当时仅十岁而已。正因为如此,我起初不敢穿。在母亲的威逼利诱下,才勉强穿上。如何威逼?她说:“这身衣服不穿,以后过年就没新衣服穿了。”穿吧,不穿不行。穿了却不敢出门,我怕。怕什么?怕村里的伙伴们嘲笑。笑什么?笑我假装城里人,明明是乡下人嘛。如此反复思量,愈发不敢出门。穿着平生第一套西装却不敢出门,真如古人所说的锦衣夜行。母亲不依不饶,穿了新衣服不出门,哪算过年?既要穿衣,还要出门。没人看出我是硬着头皮出门的,我浑身不自在。走在村道上的时候,与别人打招呼也很别扭。穿西装要腰杆挺直、脑袋昂起,不似平常穿的衣服,我哪里有过这种体验?那段不长的村路,走了好久好久,我生怕遇到任何一个认识的,遇到陌生人也怕擦肩而过。
因了这套西装,我很快“逃”回家中,不像以前总在外头疯玩,到了饭点令母亲或弟弟叫我多次才回。这是我人生第一套西装,它为我工作后穿比较正式服装消除心理芥蒂,尽管已是时隔多年。
小时候穿西装就那一回,跨火盆却是年年都有的。在自家屋前跨,还要在祖厝前跨。自家屋前只有父亲、我、弟弟三个人,母亲和妹妹不参与。到了祖厝,有几位伯伯以及他们各自的子孙,加上我们一家三口,一共三十多人,热闹极了。堂哥弄来番薯藤,下置一张易燃的纸,打火机一开,火势很快冲起,又很快壮大。不算恢宏的祖厝前,燃起熊熊烈火,通红的火焰让过年的气氛陡增几分。人从外头起步,高高跃起、跨过烈火,冲进屋里,如此一条有头有尾的路线,才算是完结。火盆只有一个,等待跨越的人有许多,得一个一个来。
边上一阵接一阵的烟花爆响与鞭炮脆响,热闹简直无边无际。
去年的小屁孩,近一年不见,简直像拔节的竹子长势喜人。满头白发的两个伯伯,总是等到年轻人都跨完,火苗将尽时才最后上阵,慢慢地跨过,慢慢地走进里屋。看着孩子们蹦蹦跳跳、年轻人欢声笑语,他们的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
对了,那时春节的跨火盆,跨是有的,火是有的,单单没有盆。至少我从小到大就没见过。就地而跨,跨过去跃过去飞过去,是年轻的感觉,也是过年的感觉。也许,大地正是火的盆吧,我自以为是地想着。
又过了一年,才惊觉时光流逝之快,好多事还来不及做,一年就又到头。年复一年,过年又过年,每个人都是在年味中熏陶、濡染、沉浸中长大的。岁月是一条长长的河流,平常日子是宽敞平坦河道上的缓缓流淌,过年这段时间则是拐弯处的急转与加速。迸溅出的水花四散,如过年的鞭炮、嬉笑、追逐、打闹,以及各种不期然却令人欣喜的声音。它们不约而同奏起的交响曲,让年味愈发浓烈、丰富、深邃、悠长,让人在匆忙、焦躁的日子里,情不自禁地回头看了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