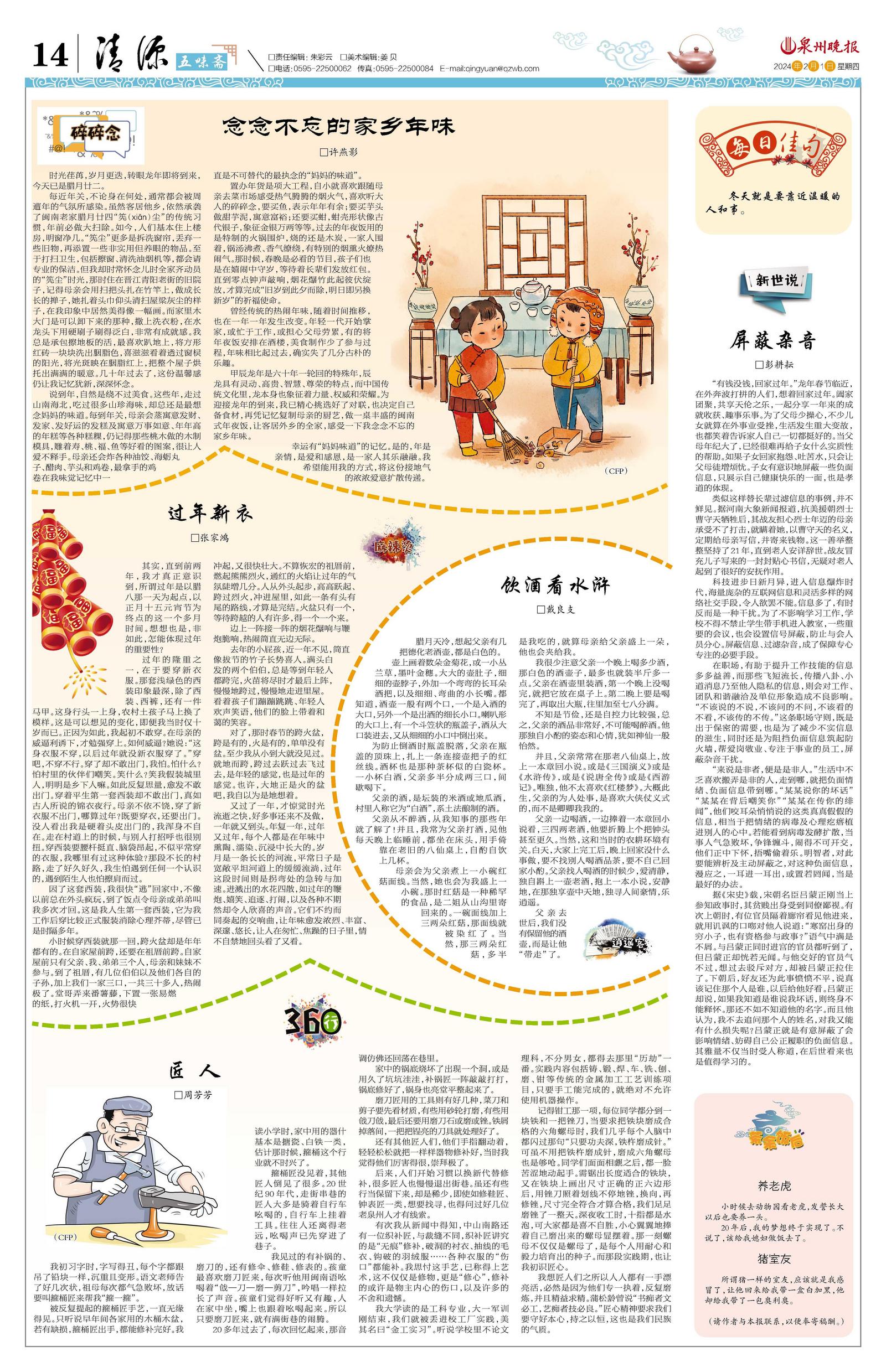我初习字时,字写得丑,每个字都跟吊了铅块一样,沉重且变形。语文老师告了好几次状,祖母每次都气急败坏,放话要叫箍桶匠来帮我“箍一箍”。
被反复提起的箍桶匠手艺,一直无缘得见。只听说早年间各家用的木桶木盆,若有缺损,箍桶匠出手,都能修补完好。我读小学时,家中用的器什基本是搪瓷、白铁一类,估计那时候,箍桶这个行业就不时兴了。
箍桶匠没见着,其他匠人倒见了很多。20世纪90年代,走街串巷的匠人大多是骑着自行车吆喝的,自行车上挂着工具。往往人还离得老远,吆喝声已先穿进了巷子。
我见过的有补锅的、磨刀的,还有修伞、修鞋、修表的。孩童最喜欢磨刀匠来,每次听他用闽南语吆喝着“戗—刀—磨—剪刀”,吟唱一样拉长了声音。孩童们觉得好听又有趣,人在家中坐,嘴上也跟着吆喝起来。所以只要磨刀匠来,就有满街巷的闹腾。
20多年过去了,每次回忆起来,那音调仿佛还回荡在巷里。
家中的锅底烧坏了出现一个洞,或是用久了坑坑洼洼,补锅匠一阵敲敲打打,锅底修好了,锅身也亮堂平整起来了。
磨刀匠用的工具则有好几种,菜刀和剪子要先看材质,有些用砂轮打磨,有些用戗刀戗,最后还要用磨刀石或磨或锉。铁屑掉落间,一把把锃亮的刀具就处理好了。
还有其他匠人们,他们手指翻动着,轻轻松松就把一样样器物修补好,当时我觉得他们厉害得很,崇拜极了。
后来,人们开始习惯以换新代替修补,很多匠人也慢慢退出街巷。虽还有些行当保留下来,却是稀少,即使如修鞋匠、钟表匠一类,想要找寻,也得问过好几位老泉州人才有线索。
有次我从新闻中得知,中山南路还有一位织补匠,与裁缝不同,织补匠讲究的是“无痕”修补,破洞的衬衣、抽线的毛衣、钩破的羽绒服……各种衣服的“伤口”都能补。我思忖这手艺,已称得上艺术,这不仅仅是修物,更是“修心”,修补的或许是物主内心的伤口,以及许多的不舍和遗憾。
我大学读的是工科专业,大一军训刚结束,我们就被丢进校工厂实践,美其名曰“金工实习”。听说学校里不论文理科,不分男女,都得去那里“历劫”一番。实践内容包括铸、锻、焊、车、铣、刨、磨、钳等传统的金属加工工艺训练项目,只要手工能完成的,就绝对不允许使用机器操作。
记得钳工那一项,每位同学都分到一块铁和一把锉刀,当要求把铁块磨成合格的六角螺母时,我们几乎每个人脑中都闪过那句“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可虽不用把铁杵磨成针,磨成六角螺母也是够呛。同学们面面相觑之后,都一脸苦涩地动起手。需锯出长度适合的铁块,又在铁块上画出尺寸正确的正六边形后,用锉刀照着划线不停地锉,换向,再修锉,尺寸完全符合才算合格,我们足足磨锉了一整天。深夜收工时,十指都是水泡,可大家都是喜不自胜,小心翼翼地捧着自己磨出来的螺母显摆着。那一刻螺母不仅仅是螺母了,是每个人用耐心和毅力培育出的种子。而那段实践期,也让我初识匠心。
我想匠人们之所以人人都有一手漂亮活,必然是因为他们专一执着,反复磨炼,并且精益求精。蒲松龄曾说“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匠心精神要求我们要守好本心,持之以恒,这也是我们民族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