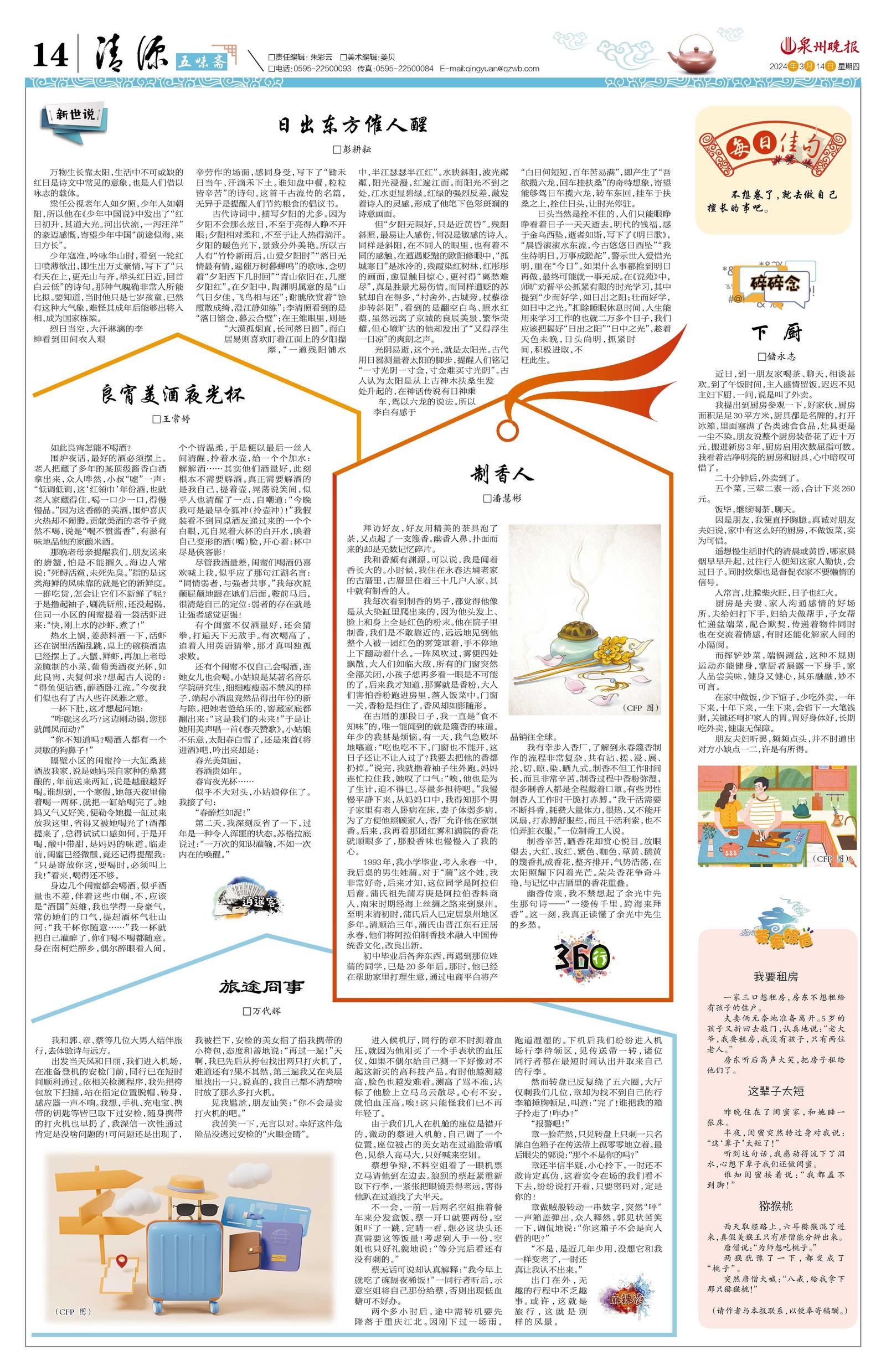拜访好友,好友用精美的茶具泡了茶,又点起了一支篾香。幽香入鼻,扑面而来的却是无数记忆碎片。
我和香颇有渊源。可以说,我是闻着香长大的。小时候,我住在永春达埔老家的古厝里,古厝里住着三十几户人家,其中就有制香的人。
我每次看到制香的男子,都觉得他像是从大染缸里爬出来的,因为他头发上、脸上和身上全是红色的粉末。他在院子里制香,我们是不敢靠近的,远远地见到他整个人被一团红色的雾笼罩着,手不停地上下翻动着什么。一阵风吹过,雾便四处飘散,大人们如临大敌,所有的门窗突然全部关闭,小孩子想再多看一眼是不可能的了。后来我才知道,那雾就是香粉,大人们害怕香粉跑进房里,落入饭菜中。门窗一关,香粉是挡住了,香风却如影随形。
在古厝的那段日子,我一直是“食不知味”的,唯一能闻到的就是篾香的味道。年少的我甚是烦恼。有一天,我气急败坏地嚷道:“吃也吃不下,门窗也不能开,这日子还让不让人过了?我要去把他的香都扔掉。”说完,我就撸着袖子往外跑。妈妈连忙拉住我,她叹了口气:“唉,他也是为了生计,迫不得已。尽量多担待吧。”我慢慢平静下来,从妈妈口中,我得知那个男子家里有老人卧病在床,妻子体弱多病,为了方便他照顾家人,香厂允许他在家制香。后来,我再看那团红雾和满院的香花就顺眼多了,那股香味也慢慢入了我的心。
1993年,我小学毕业,考入永春一中,我后桌的男生姓蒲。对于“蒲”这个姓,我非常好奇,后来才知,这位同学是阿拉伯后裔。蒲氏祖先蒲寿庚是阿拉伯香料商人,南宋时期经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泉州。至明末清初时,蒲氏后人已定居泉州地区多年。清顺治三年,蒲氏由晋江东石迁居永春,他们将阿拉伯制香技术融入中国传统香文化,改良出新。
初中毕业后各奔东西,再遇到那位姓蒲的同学,已是20多年后。那时,他已经在帮助家里打理生意,通过电商平台将产品销往全球。
我有幸步入香厂,了解到永春篾香制作的流程非常复杂,共有沾、搓、浸、展、抡、切、晾、染、晒九式。制香不但工作时间长,而且非常辛苦。制香过程中香粉弥漫,很多制香人都是全程戴着口罩。有些男性制香人工作时干脆打赤膊。“我干活需要不断抖香,耗费大量体力,很热,又不能开风扇,打赤膊舒服些,而且干活利索,也不怕弄脏衣服。”一位制香工人说。
制香辛苦,晒香花却赏心悦目。放眼望去,大红、玫红、紫色、咖色、草黄、鹅黄的篾香扎成香花,整齐排开,气势浩荡,在太阳照耀下闪着光芒。朵朵香花争奇斗艳,与记忆中古厝里的香花重叠。
幽香传来,我不禁想起了余光中先生那句诗——“一缕传千里,跨海来拜香”。这一刻,我真正读懂了余光中先生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