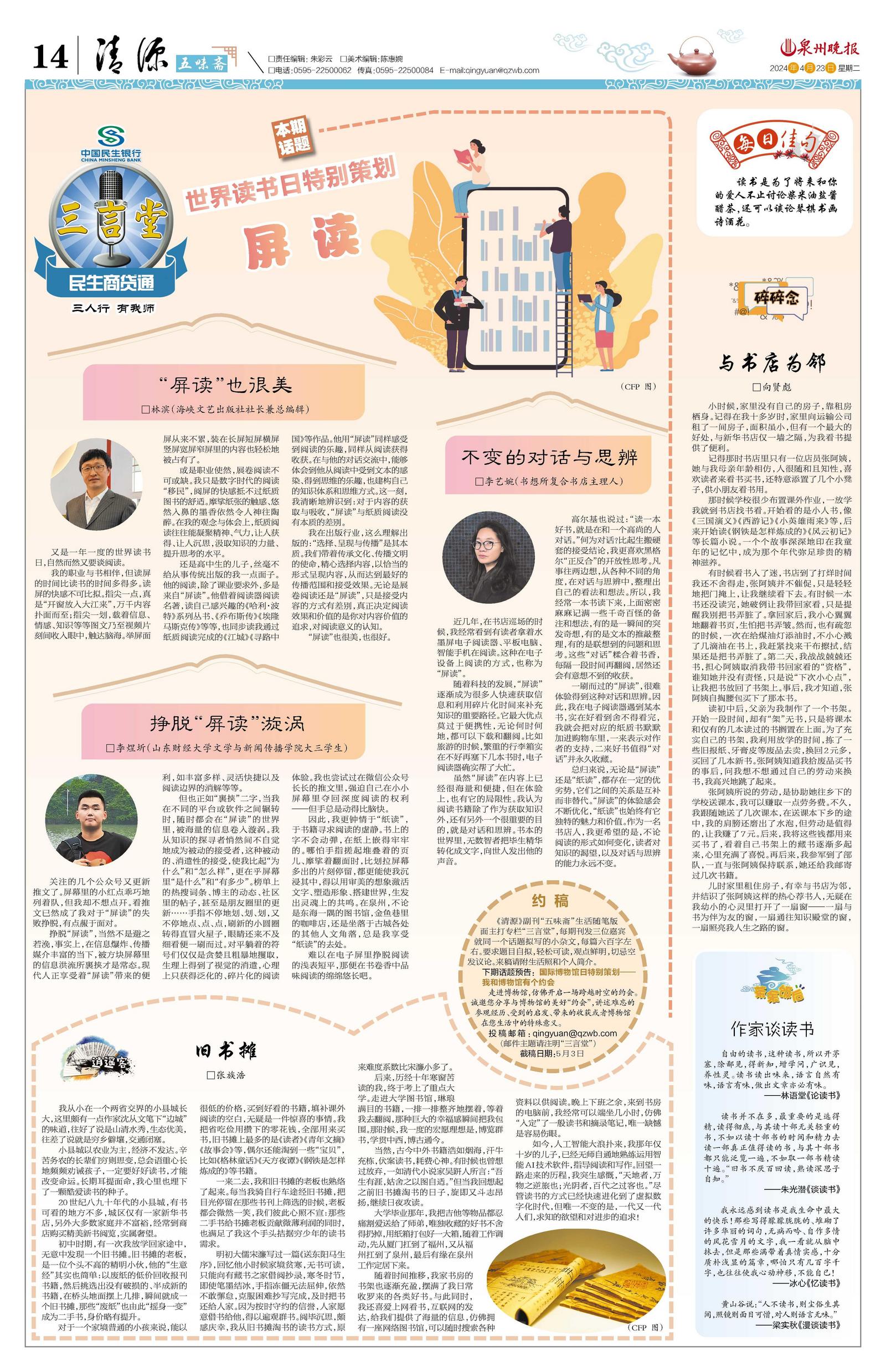□张族浩
我从小在一个两省交界的小县城长大,这里颇有一点作家沈从文笔下“边城”的味道,往好了说是山清水秀,生态优美,往差了说就是穷乡僻壤,交通闭塞。
小县城以农业为主,经济不发达。辛苦务农的长辈们穷则思变,总会语重心长地频频劝诫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改变命运。长期耳提面命,我心里也埋下了一颗酷爱读书的种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小县城,有书可看的地方不多,城区仅有一家新华书店,另外大多数家庭并不富裕,经常到商店购买精美新书阅览,实属奢望。
初中时期,有一次我放学回家途中,无意中发现一个旧书摊。旧书摊的老板,是一位个头不高的精明小伙,他的“生意经”其实也简单:以废纸的低价回收报刊书籍,然后挑选出没有破损的、半成新的书籍,在桥头地面摆上几排,瞬间就成一个旧书摊,那些“废纸”也由此“摇身一变”成为二手书,身价略有提升。
对于一个家境普通的小孩来说,能以很低的价格,买到好看的书籍,填补课外阅读的空白,无疑是一件惊喜的事情。我把省吃俭用攒下的零花钱,全部用来买书,旧书摊上最多的是《读者》《青年文摘》《故事会》等,偶尔还能淘到一些“宝贝”,比如《格林童话》《天方夜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籍。
一来二去,我和旧书摊的老板也熟络了起来。每当我骑自行车途经旧书摊,把目光停留在那些书刊上筛选的时候,老板都会微然一笑,我们彼此心照不宣:那些二手书给书摊老板贡献微薄利润的同时,也满足了我这个手头拮据穷少年的读书需求。
明初大儒宋濂写过一篇《送东阳马生序》,回忆他小时候家境贫寒,无书可读,只能向有藏书之家借阅抄录,寒冬时节,即使笔墨结冰,手指冻僵无法屈伸,依然不敢懈怠,克服困难抄写完成,及时把书还给人家。因为按时守约的信誉,人家愿意借书给他,得以遍观群书。阅毕沉思,颇感庆幸,我从旧书摊淘书的读书方式,原来难度系数比宋濂小多了。
后来,历经十年寒窗苦读的我,终于考上了重点大学。走进大学图书馆,琳琅满目的书籍,一排一排整齐地摆着,等着我去翻阅,那种巨大的幸福感瞬间把我包围。那时候,我一度的宏愿理想是,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博古通今。
当然,古今中外书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伏案读书,耗费心神。有时候也曾想过放弃,一如清代小说家吴趼人所言:“吾生有涯,姑舍之以图自适。”但当我回想起之前旧书摊淘书的日子,旋即又斗志昂扬,继续日夜攻读。
大学毕业那年,我把吉他等物品都忍痛割爱送给了师弟,唯独收藏的好书不舍得扔掉,用纸箱打包好一大箱,随着工作调动,先从厦门扛到了福州,又从福州扛到了泉州,最后有缘在泉州工作定居下来。
随着时间推移,我家书房的书架也逐渐充盈,摆满了我日常收罗来的各类好书。与此同时,我还喜爱上网看书,互联网的发达,给我们提供了海量的信息,仿佛拥有一座网络图书馆,可以随时搜索各种资料以供阅读。晚上下班之余,来到书房的电脑前,我经常可以端坐几小时,仿佛“入定”了一般读书和摘录笔记,唯一缺憾是容易伤眼。
如今,人工智能大浪扑来,我那年仅十岁的儿子,已经无师自通地熟练运用智能AI技术软件,指导阅读和写作。回望一路走来的历程,我突生感慨,“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尽管读书的方式已经快速进化到了虚拟数字化时代,但唯一不变的是,一代又一代人们,求知的欲望和对进步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