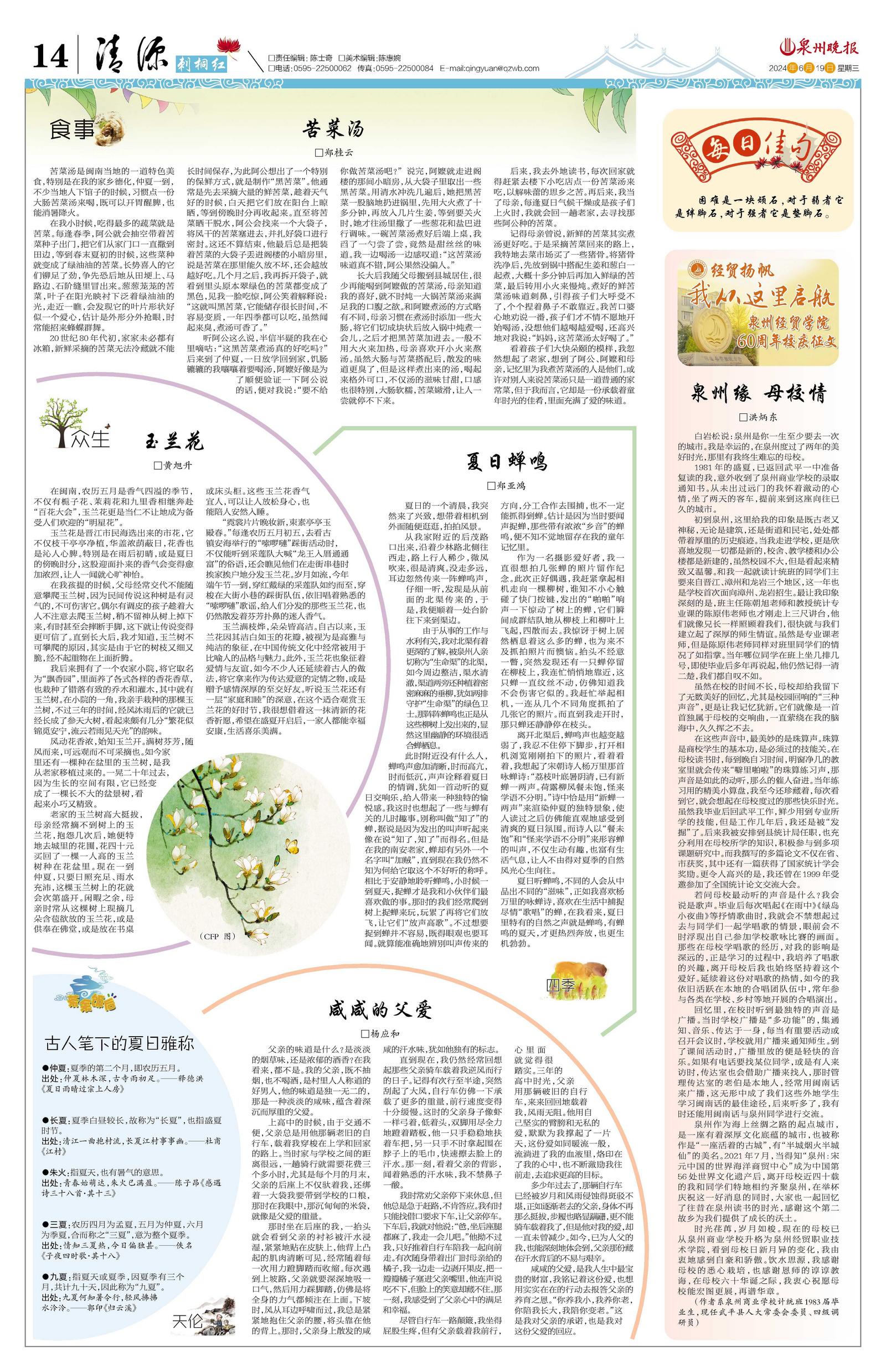□郑桂云
苦菜汤是闽南当地的一道特色美食,特别是在我的家乡德化,仲夏一到,不少当地人下馆子的时候,习惯点一份大肠苦菜汤来喝,既可以开胃醒脾,也能消暑降火。
在我小时候,吃得最多的蔬菜就是苦菜。每逢春季,阿公就会抽空带着苦菜种子出门,把它们从家门口一直撒到田边,等到春末夏初的时候,这些菜种就变成了绿油油的苦菜。长势喜人的它们铆足了劲,争先恐后地从田埂上、马路边、石阶缝里冒出来。葱葱茏茏的苦菜,叶子在阳光映衬下泛着绿油油的光,走近一瞧,会发现它的叶片形状好似一个爱心,估计是外形分外抢眼,时常能招来蜂蝶群舞。
20世纪80年代初,家家未必都有冰箱,新鲜采摘的苦菜无法冷藏就不能长时间保存,为此阿公想出了一个特别的保鲜方式,就是制作“黑苦菜”。他通常是先去采摘大量的鲜苦菜,趁着天气好的时候,白天把它们放在阳台上晾晒,等到傍晚时分再收起来。直至将苦菜晒干脱水,阿公会找来一个大袋子,将风干的苦菜塞进去,并扎好袋口进行密封。这还不算结束,他最后总是把装着苦菜的大袋子丢进阁楼的小暗房里,说是苦菜在那里能久放不坏,还会越放越好吃。几个月之后,我再拆开袋子,就看到里头原本翠绿色的苦菜都变成了黑色,见我一脸吃惊,阿公笑着解释说:“这就叫黑苦菜,它能储存很长时间,不容易变质,一年四季都可以吃,虽然闻起来臭,煮汤可香了。”
听阿公这么说,半信半疑的我在心里嘀咕:“这黑苦菜煮汤真的好吃吗?”后来到了仲夏,一日放学回到家,饥肠辘辘的我嚷嚷着要喝汤,阿嬷好像是为了顺便验证一下阿公说的话,便对我说:“要不给你做苦菜汤吧?” 说完,阿嬷就走进阁楼的那间小暗房,从大袋子里取出一些黑苦菜。用清水冲洗几遍后,她把黑苦菜一股脑地扔进锅里,先用大火煮了十多分钟,再放入几片生姜,等到要关火时,她才往汤里撒了一些葱花和盐巴进行调味。一碗苦菜汤煮好后端上桌,我舀了一勺尝了尝,竟然是甜丝丝的味道。我一边喝汤一边感叹道:“这苦菜汤味道真不错,阿公果然没骗人。”
长大后我随父母搬到县城居住,很少再能喝到阿嬷做的苦菜汤,母亲知道我的喜好,就不时炖一大锅苦菜汤来满足我的口腹之欲。和阿嬷煮汤的方式略有不同,母亲习惯在煮汤时添加一些大肠,将它们切成块状后放入锅中炖煮一会儿,之后才把黑苦菜加进去。一般不用大火来加热,母亲喜欢开小火来熬汤。虽然大肠与苦菜搭配后,散发的味道更臭了,但是这样煮出来的汤,喝起来格外可口,不仅汤的滋味甘甜,口感也很特别,大肠软糯,苦菜嫩滑,让人一尝就停不下来。
后来,我去外地读书,每次回家就得赶紧去楼下小吃店点一份苦菜汤来吃,以解味蕾的思乡之苦。再后来,我当了母亲,每逢夏日气候干燥或是孩子们上火时,我就会回一趟老家,去寻找那些阿公种的苦菜。
记得母亲曾说,新鲜的苦菜其实煮汤更好吃。于是采摘苦菜回来的路上,我特地去菜市场买了一些猪骨。将猪骨洗净后,先放到锅中搭配生姜和葱白一起煮,大概十多分钟后再加入鲜绿的苦菜,最后转用小火来慢炖。煮好的鲜苦菜汤味道刺鼻,引得孩子们大呼受不了,个个捏着鼻子不敢靠近。我苦口婆心地劝说一番,孩子们才不情不愿地开始喝汤,没想他们越喝越爱喝,还高兴地对我说:“妈妈,这苦菜汤太好喝了。”
看着孩子们大快朵颐的模样,我忽然想起了老家,想到了阿公、阿嬷和母亲,记忆里为我煮苦菜汤的人是他们。或许对别人来说苦菜汤只是一道普通的家常菜,但于我而言,它却是一份承载着童年时光的佳肴,里面充满了爱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