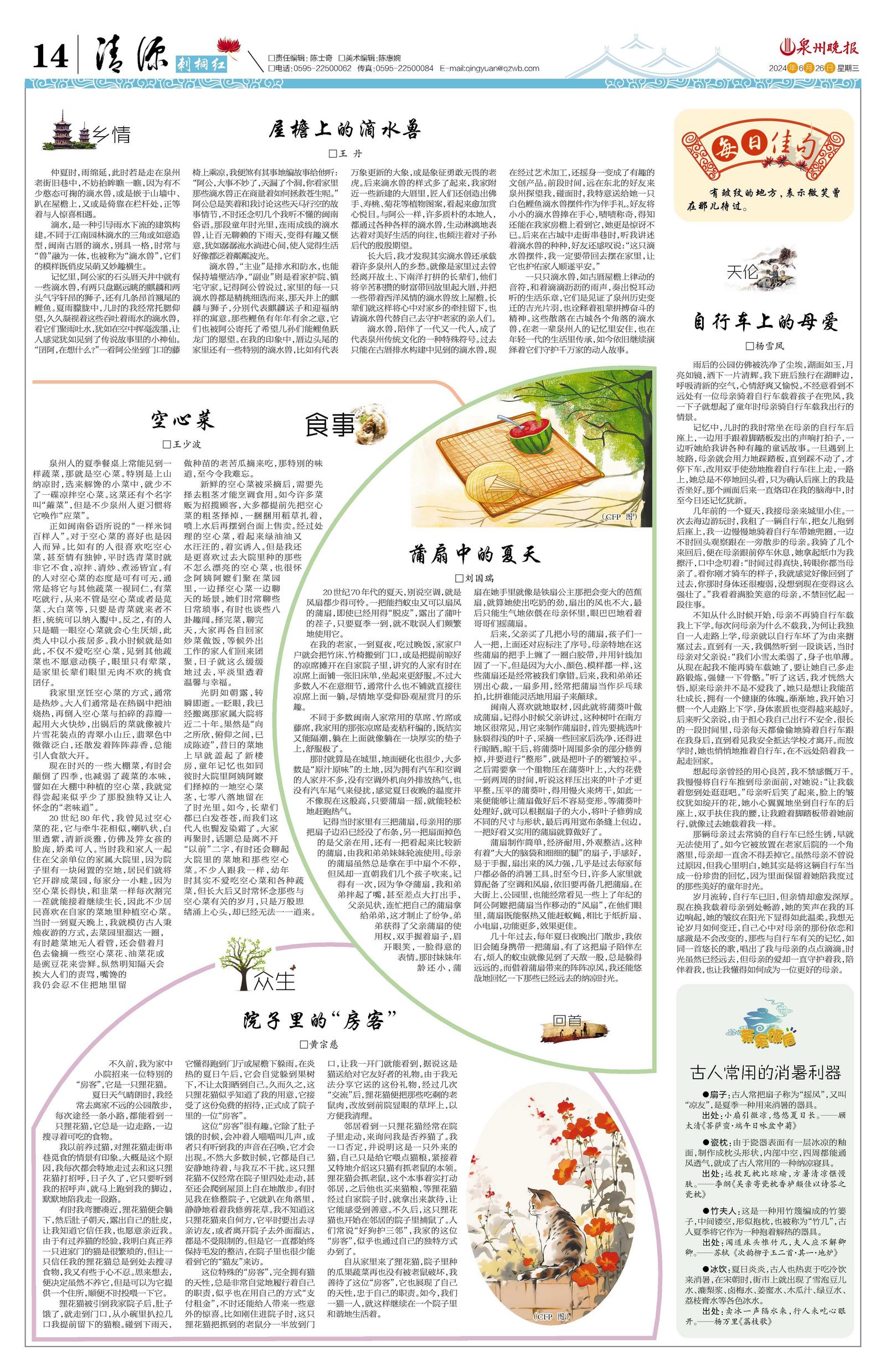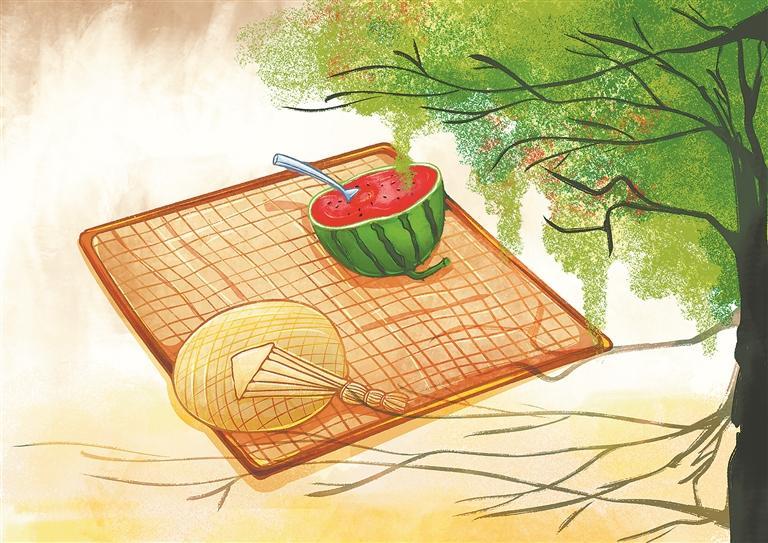20世纪70年代的夏天,别说空调,就是风扇都少得可怜。一把能挡蚊虫又可以扇风的蒲扇,即使已经用得“脱皮”,露出了蒲叶的茬子,只要夏季一到,就不耽误人们频繁地使用它。
在我的老家,一到夏夜,吃过晚饭,家家户户就会把竹床、竹椅搬到门口,或是把提前晾好的凉席摊开在自家院子里,讲究的人家有时在凉席上面铺一张旧床单,坐起来更舒服。不过大多数人不在意细节,通常什么也不铺就直接往凉席上面一躺,尽情地享受仰卧观星赏月的乐趣。
不同于多数闽南人家常用的草席、竹席或藤席,我家用的那张凉席是麦秸秆编的,既结实又能隔潮,躺在上面就像躺在一块厚实的垫子上,舒服极了。
那时就算是在城里,地面硬化也很少,大多数是“原汁原味”的土地,因为拥有汽车和空调的人家并不多,没有空调外机向外排放热气,也没有汽车尾气来侵扰,感觉夏日夜晚的温度并不像现在这般高,只要蒲扇一摇,就能轻松地赶跑热气。
记得当时家里有三把蒲扇,母亲用的那把扇子边沿已经没了布条,另一把扇面掉色的是父亲在用,还有一把看起来比较新的蒲扇,由我和弟弟妹妹轮流使用。母亲的蒲扇虽然总是拿在手中扇个不停,但风却一直朝我们几个孩子吹来。记得有一次,因为争夺蒲扇,我和弟弟拌起了嘴,甚至差点大打出手,父亲见状,连忙把自己的蒲扇拿给弟弟,这才制止了纷争。弟弟获得了父亲蒲扇的使用权,双手握着扇子,眉开眼笑,一脸得意的表情。那时妹妹年龄还小,蒲扇在她手里就像是铁扇公主那把会变大的芭蕉扇,就算她使出吃奶的劲,扇出的风也不大,最后只能生气地依偎在母亲怀里,眼巴巴地看着哥哥们摇蒲扇。
后来,父亲买了几把小号的蒲扇,孩子们一人一把,上面还对应标注了序号。母亲特地在这些蒲扇的把手上缠了一圈白胶带,并用针线加固了一下。但是因为大小、颜色、模样都一样,这些蒲扇还是经常被我们拿错。后来,我和弟弟还别出心裁,一扇多用,经常把蒲扇当作乒乓球拍,比拼谁能灵活地用扇子来颠球。
闽南人喜欢就地取材,因此就将蒲葵叶做成蒲扇。记得小时候父亲讲过,这种树叶在南方地区很常见,用它来制作蒲扇时,首先要挑选叶脉裂得浅的叶子,采摘一些回家后洗净,还得进行晾晒。晾干后,将蒲葵叶周围多余的部分修剪掉,并要进行“整形”,就是把叶子的褶皱拉平。之后需要拿一个重物压在蒲葵叶上,大约花费一到两周的时间,听说这样压出来的叶子才更平整。压平的蒲葵叶,得用慢火来烤干,如此一来便能够让蒲扇做好后不容易变形。等蒲葵叶处理好,就可以根据扇子的大小,将叶子修剪成不同的尺寸与形状,最后再用宽布条缝上包边,一把好看又实用的蒲扇就算做好了。
蒲扇制作简单,经济耐用,外观整洁。这种有着“大大的脑袋和细细的腿”的扇子,手感好,易于手握,扇出来的风力强,几乎是过去每家每户都必备的消暑工具。时至今日,许多人家里就算配备了空调和风扇,依旧要再备几把蒲扇。在大街上、公园里,也能经常看见一些上了年纪的阿公阿嬷把蒲扇当作移动的“风扇”,在他们眼里,蒲扇既能驱热又能赶蚊蝇,相比于纸折扇、小电扇,功能更多,效果更佳。
几十年过去,每年夏日夜晚出门散步,我依旧会随身携带一把蒲扇。有了这把扇子陪伴左右,烦人的蚊虫就像见到了天敌一般,总是躲得远远的。而借着蒲扇带来的阵阵凉风,我还能悠哉地回忆一下那些已经远去的纳凉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