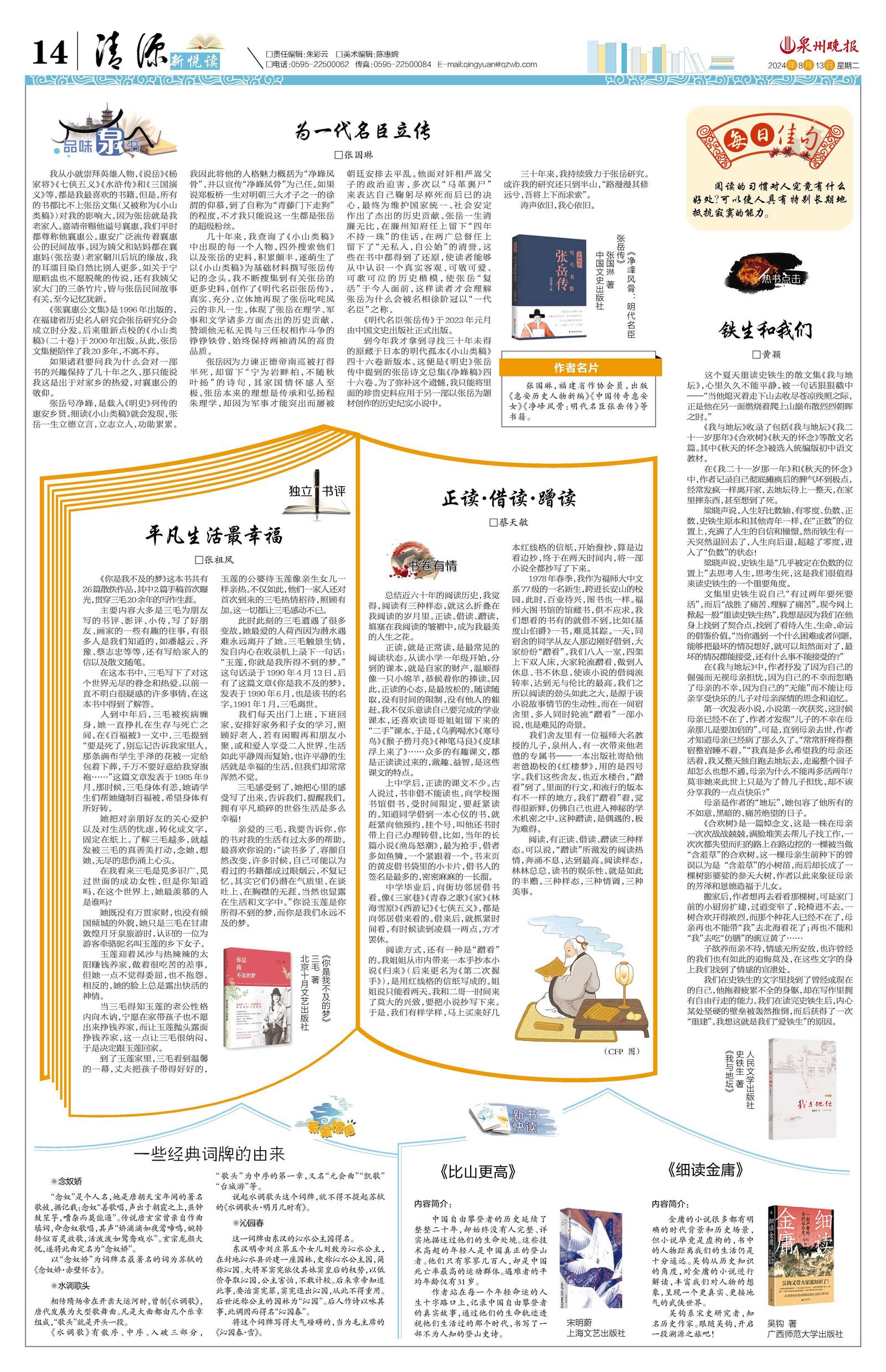这个夏天重读史铁生的散文集《我与地坛》,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被一句话狠狠戳中——“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
《我与地坛》收录了包括《我与地坛》《我二十一岁那年》《合欢树》《秋天的怀念》等散文名篇。其中《秋天的怀念》被选入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
在《我二十一岁那一年》和《秋天的怀念》中,作者记录自己彻底瘫痪后的脾气坏到极点,经常发疯一样离开家,去地坛待上一整天,在家里摔东西,甚至想到了死。
梁晓声说,人生好比数轴,有零度、负数、正数,史铁生原本和其他青年一样,在“正数”的位置上,充满了人生的自信和憧憬。然而铁生有一天突然退回去了,人生向后退,超越了零度,进入了“负数”的状态!
梁晓声说,史铁生是“几乎被定在负数的位置上”去思考人生,思考生死,这是我们很值得来读史铁生的一个重要角度。
文集里史铁生说自己“有过两年要死要活”,而后“战胜了痛苦、理解了痛苦”。现今网上掀起一股“重读史铁生热”,我想是因为我们在他身上找到了契合点,找到了看待人生、生命、命运的借鉴价值。“当你遇到一个什么困难或者问题,能够把最坏的情况想好,就可以坦然面对了,最坏的情况都能接受,还有什么事不能接受的?”
在《我与地坛》中,作者抒发了因为自己的倔强而无视母亲担忧,因为自己的不幸而忽略了母亲的不幸,因为自己的“无能”而不能让母亲享受快乐的儿子对母亲深情的思念和追忆。
第一次发表小说,小说第一次获奖,这时候母亲已经不在了,作者才发现“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是要加倍的”。可是,直到母亲去世,作者才知道母亲已经病了那么久了。“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我又整天独自跑去地坛去,走遍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不能再多活两年?莫非她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
母亲是作者的“地坛”,她包容了他所有的不如意,黑暗的、痛苦绝望的日子。
《合欢树》是一篇悼念文,这是一株在母亲一次次战战兢兢,满脸堆笑去帮儿子找工作,一次次都失望而归的路上在路边挖的一棵被当做“含羞草”的合欢树。这一棵母亲生前种下的曾误以为是 “含羞草”的小树苗,而后却长成了一棵树影婆娑的参天大树,作者以此来象征母亲的芳泽和恩德造福于儿女。
搬家后,作者想再去看看那棵树,可是家门前的小厨房扩建,过道变窄了,轮椅进不去。一树合欢开得浓烈,而那个种花人已经不在了,母亲再也不能带“我”去北海看花了;再也不能和“我”去吃“仿膳”的豌豆黄了……
子欲养而亲不待,情感无所安放,也许曾经的我们也有如此的追悔莫及,在这些文字的身上我们找到了情感的宣泄处。
我们在史铁生的文字里找到了曾经或现在的自己,他拖着疲累不全的身躯,却在写作里拥有自由行走的能力。我们在读完史铁生后,内心某处坚硬的壁垒被轰然推倒,而后获得了一次“重建”。我想这就是我们“爱铁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