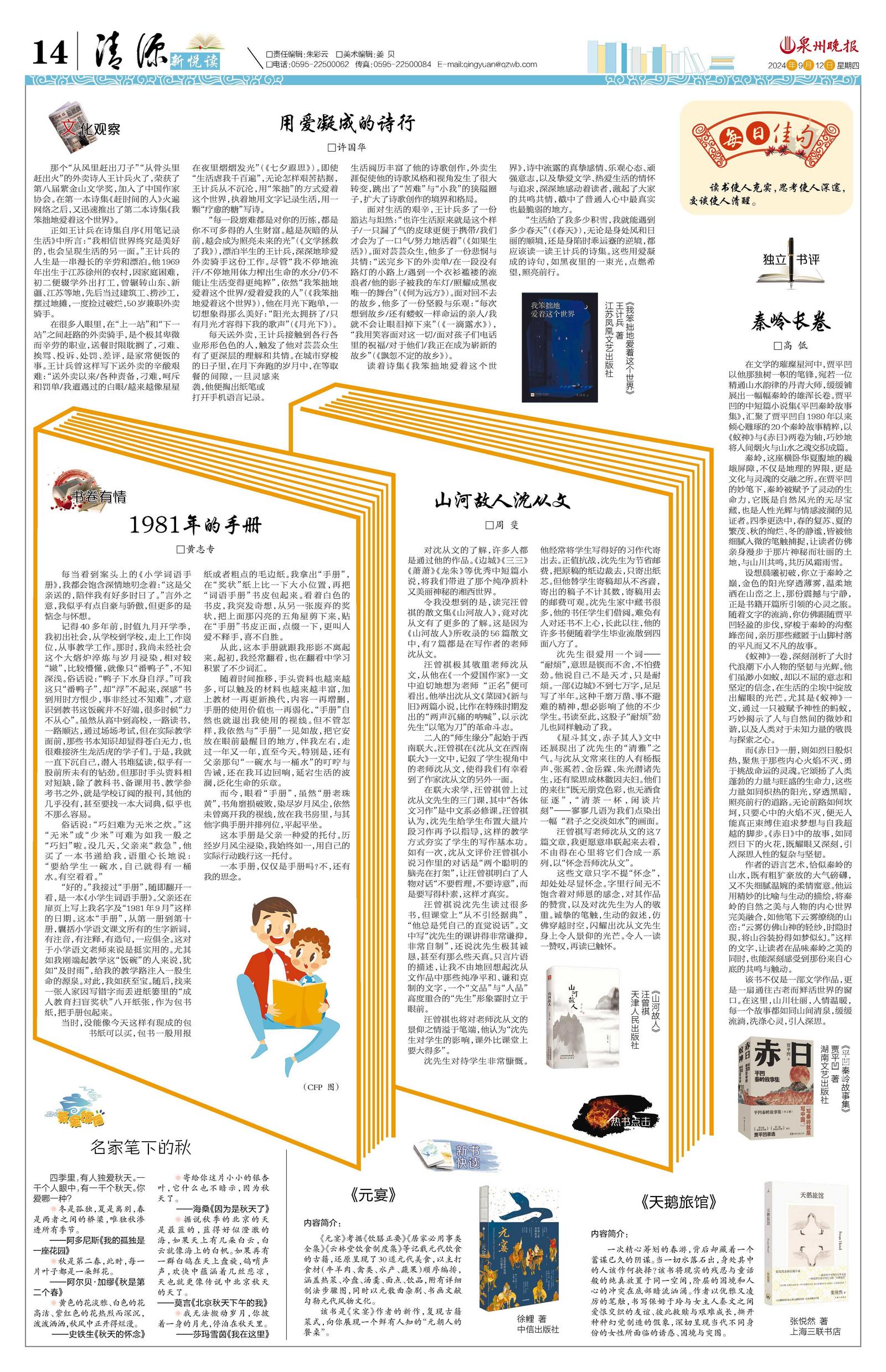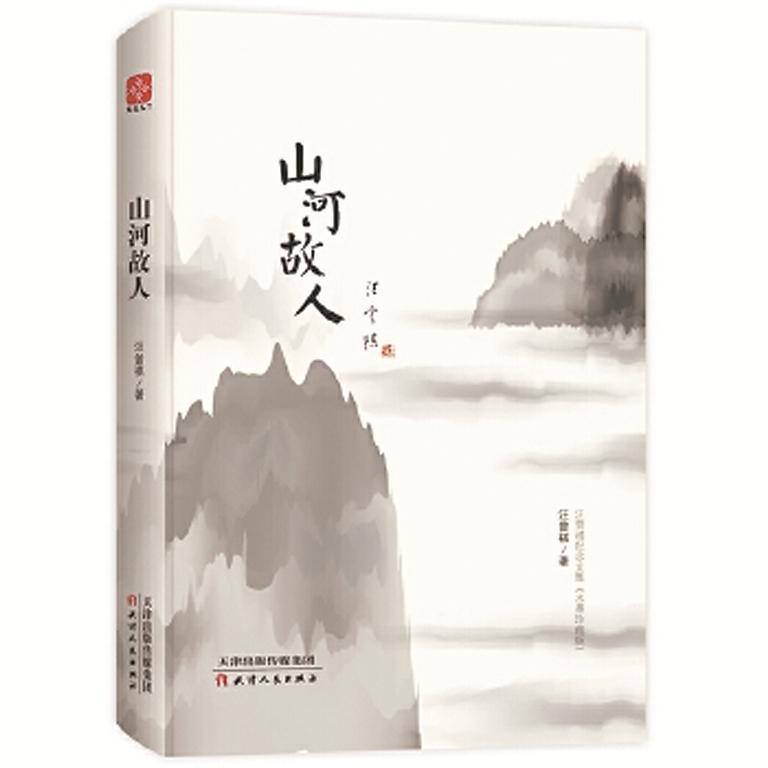对沈从文的了解,许多人都是通过他的作品。《边城》《三三》《萧萧》《龙朱》等优秀中短篇小说,将我们带进了那个纯净质朴又美丽神秘的湘西世界。
令我没想到的是,读完汪曾祺的散文集《山河故人》,竟对沈从文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是因为《山河故人》所收录的56篇散文中,有7篇都是在写作者的老师沈从文。
汪曾祺极其敬重老师沈从文,从他在《一个爱国作家》一文中迫切地想为老师 “正名”便可看出。他举出沈从文《菜园》《新与旧》两篇小说,比作在特殊时期发出的“两声沉痛的呐喊”,以示沈先生“以笔为刀”的革命斗志。
二人的“师生缘分”起始于西南联大。汪曾祺在《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一文中,记叙了学生视角中的老师沈从文,使得我们有幸看到了作家沈从文的另外一面。
在联大求学,汪曾祺曾上过沈从文先生的三门课,其中“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必修课。汪曾祺认为,沈先生给学生布置大量片段习作再予以指导,这样的教学方式夯实了学生的写作基本功。如有一次,沈从文评价汪曾祺小说习作里的对话是“两个聪明的脑壳在打架”,让汪曾祺明白了人物对话“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而是要写得朴素,这样才真实。
汪曾祺说沈先生读过很多书,但课堂上“从不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文中写“沈先生的课讲得非常谦抑,非常自制”,还说沈先生极其诚恳,甚至有那么些天真。只言片语的描述,让我不由地回想起沈从文作品中那些纯净平和、谦和克制的文字,一个“文品”与“人品”高度重合的“先生”形象霎时立于眼前。
汪曾祺也将对老师沈从文的景仰之情溢于笔端,他认为“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
沈先生对待学生非常慷慨。他经常将学生写得好的习作代寄出去。正值抗战,沈先生为节省邮费,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寄出纸芯。但他替学生寄稿却从不吝啬,寄出的稿子不计其数,寄稿用去的邮费可观。沈先生家中藏书很多,他的书任学生们借阅。难免有人对还书不上心,长此以往,他的许多书便随着学生毕业流散到四面八方了。
沈先生很爱用一个词——“耐烦”,意思是锲而不舍,不怕费劲。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一部《边城》不到七万字,足足写了半年。这种千磨万凿、事不避难的精神,想必影响了他的不少学生。书读至此,这股子“耐烦”劲儿也同样触动了我。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文中还展现出了沈先生的“清雅”之气。与沈从文常来往的人有杨振声、张奚若、金岳霖、朱光潜诸先生,还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他们的来往“既无朋党色彩,也无酒食征逐”,“清茶一杯,闲谈片刻”——寥寥几语为我们点染出一幅 “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画面。
汪曾祺写老师沈从文的这7篇文章,我更愿意串联起来去看,不由得在心里将它们合成一系列,以“怀念吾师沈从文”。
这些文章只字不提“怀念”,却处处尽显怀念。字里行间无不饱含着对师恩的感念,对其作品的赞赏,以及对沈先生为人的敬重。诚挚的笔触,生动的叙述,仿佛穿越时空,闪耀出沈从文先生身上令人景仰的光芒。令人一读一赞叹,再读已触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