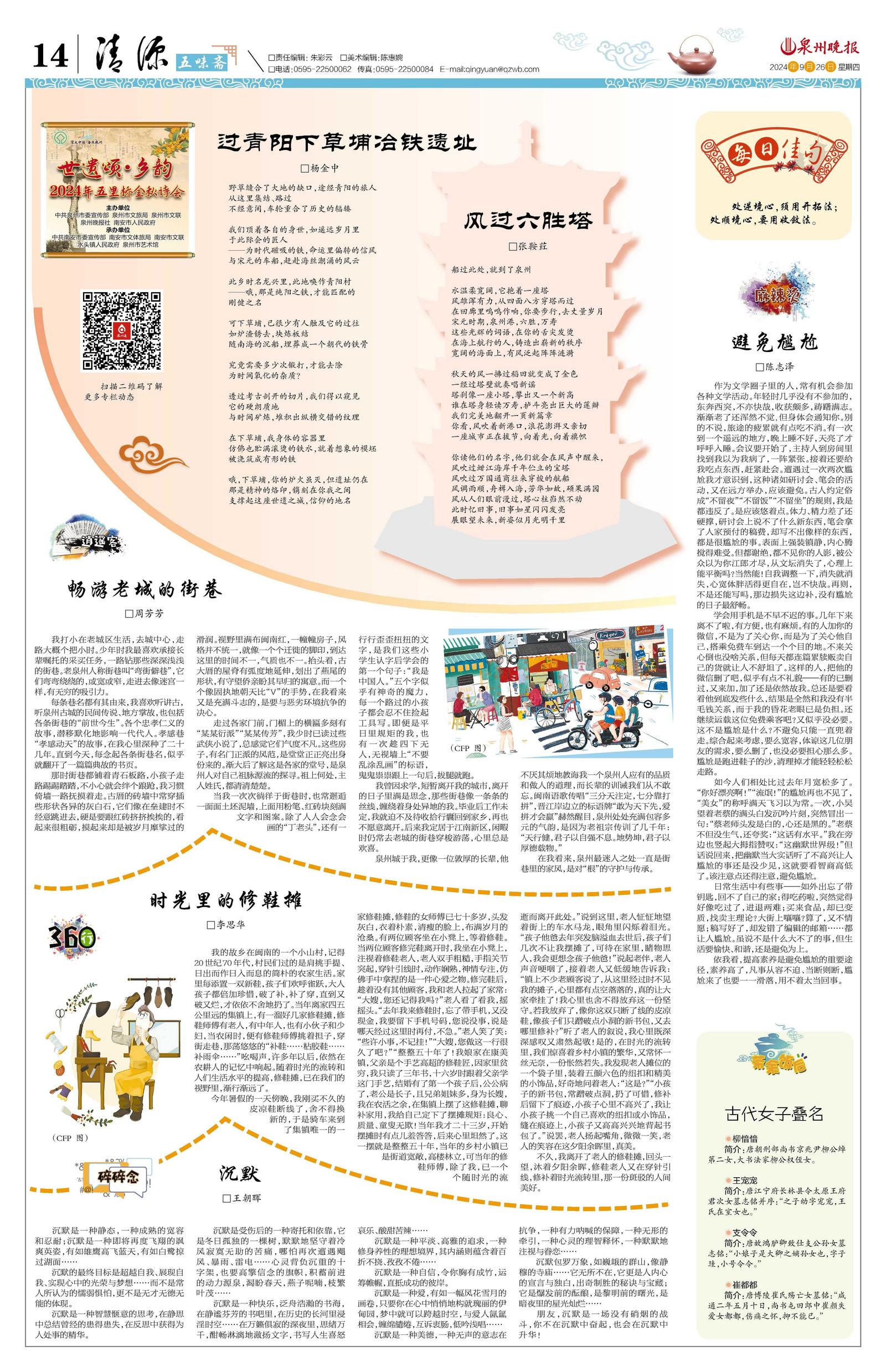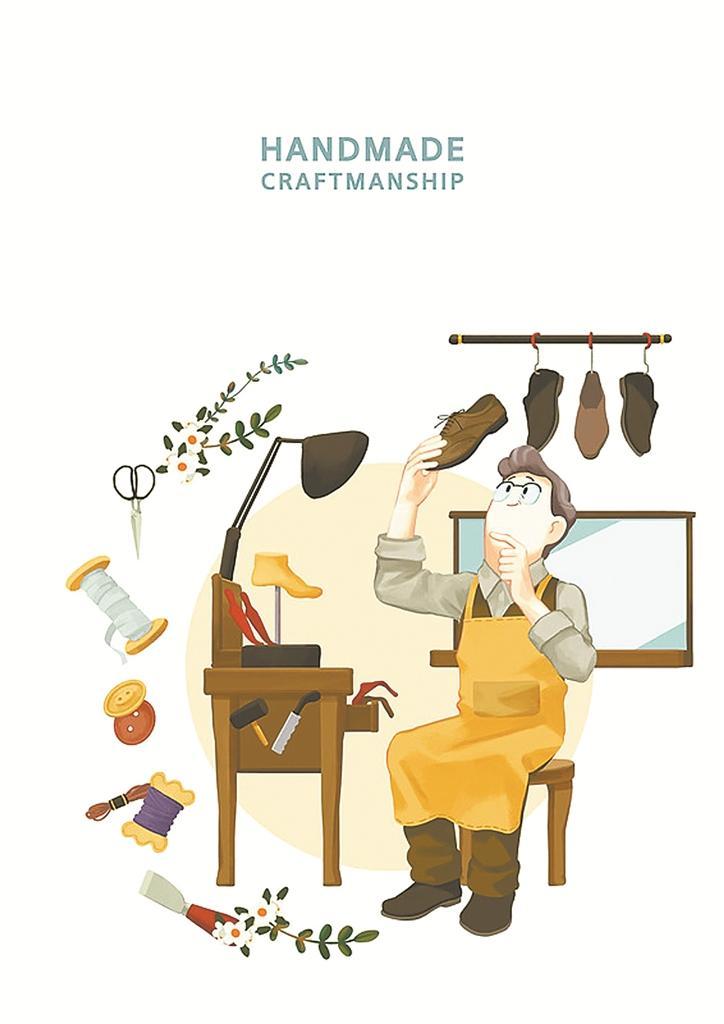我的故乡在闽南的一个小山村,记得20世纪70年代,村民们过的是肩挑手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简朴的农家生活。家里每添置一双新鞋,孩子们欢呼雀跃,大人孩子都倍加珍惜,破了补,补了穿,直到又破又烂,才依依不舍地扔了。当年离家四五公里远的集镇上,有一溜好几家修鞋摊,修鞋师傅有老人,有中年人,也有小伙子和少妇,当农闲时,便有修鞋师傅挑着担子,穿街走巷,那荡悠悠的“补鞋……粘胶鞋……补雨伞……”吆喝声,许多年以后,依然在农耕人的记忆中响起。随着时光的流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修鞋摊,已在我们的视野里,渐行渐远了。
今年暑假的一天傍晚,我刚买不久的皮凉鞋断线了,舍不得换新的,于是骑车来到了集镇唯一的一家修鞋摊,修鞋的女师傅已七十多岁,头发灰白,衣着朴素,清瘦的脸上,布满岁月的沧桑。有两位顾客坐在小凳上,等着修鞋。当两位顾客修完鞋离开时,我坐在小凳上,注视着修鞋老人,老人双手粗糙,手指关节突起,穿针引线时,动作娴熟,神情专注,仿佛手中拿捏的是一件心爱之物。修完鞋后,趁着没有其他顾客,我和老人拉起了家常:“大嫂,您还记得我吗?”老人看了看我,摇摇头。“去年我来修鞋时,忘了带手机,又没现金,我要留下手机号码,您说没事,说是哪天经过这里时再付,不急。”老人笑了笑:“些许小事,不记挂!”“大嫂,您做这一行很久了吧?”“整整五十年了!我娘家在康美镇,父亲是个手艺高超的修鞋匠,因家里贫穷,我只读了三年书,十六岁时跟着父亲学这门手艺,结婚有了第一个孩子后,公公病了,老公是长子,且兄弟姐妹多,身为长嫂,我在农活之余,在集镇上摆了这修鞋摊,聊补家用,我给自己定下了摆摊规矩:良心、质量、童叟无欺!当年我才二十三岁,开始摆摊时有点儿羞答答,后来心里坦然了。这一摆就是整整五十年,当年的乡村小镇已是街道宽敞,高楼林立,可当年的修鞋师傅,除了我,已一个个随时光的流逝而离开此处。”说到这里,老人怔怔地望着街上的车水马龙,眼角里闪烁着泪光。“孩子他爸去年突发脑溢血去世后,孩子们几次不让我摆摊了,可待在家里,睹物思人,我会更想念孩子他爸!”说起老伴,老人声音哽咽了,接着老人又低缓地告诉我:“镇上不少老顾客说了,从这里经过时不见我的摊子,心里都有点空落落的,真的让大家牵挂了!我心里也舍不得放弃这一份坚守。若我放弃了,像你这双只断了线的皮凉鞋,像孩子们只蹭破点小洞的新书包,又去哪里修补?”听了老人的叙说,我心里既深深感叹又肃然起敬!是的,在时光的流转里,我们惊喜着乡村小镇的繁华,又常怀一丝无奈,一份怅然若失。我发现老人摊位的一个袋子里,装着五颜六色的纽扣和精美的小饰品,好奇地问着老人:“这是?”“小孩子的新书包,常蹭破点洞,扔了可惜,修补后留下了痕迹,小孩子心里不高兴了,我让小孩子挑一个自己喜欢的纽扣或小饰品,缝在痕迹上,小孩子又高高兴兴地背起书包了。”说罢,老人扬起嘴角,微微一笑,老人的笑容在这夕阳余晖里,真美。
不久,我离开了老人的修鞋摊,回头一望,沐着夕阳余晖,修鞋老人又在穿针引线,修补着时光流转里,那一份斑驳的人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