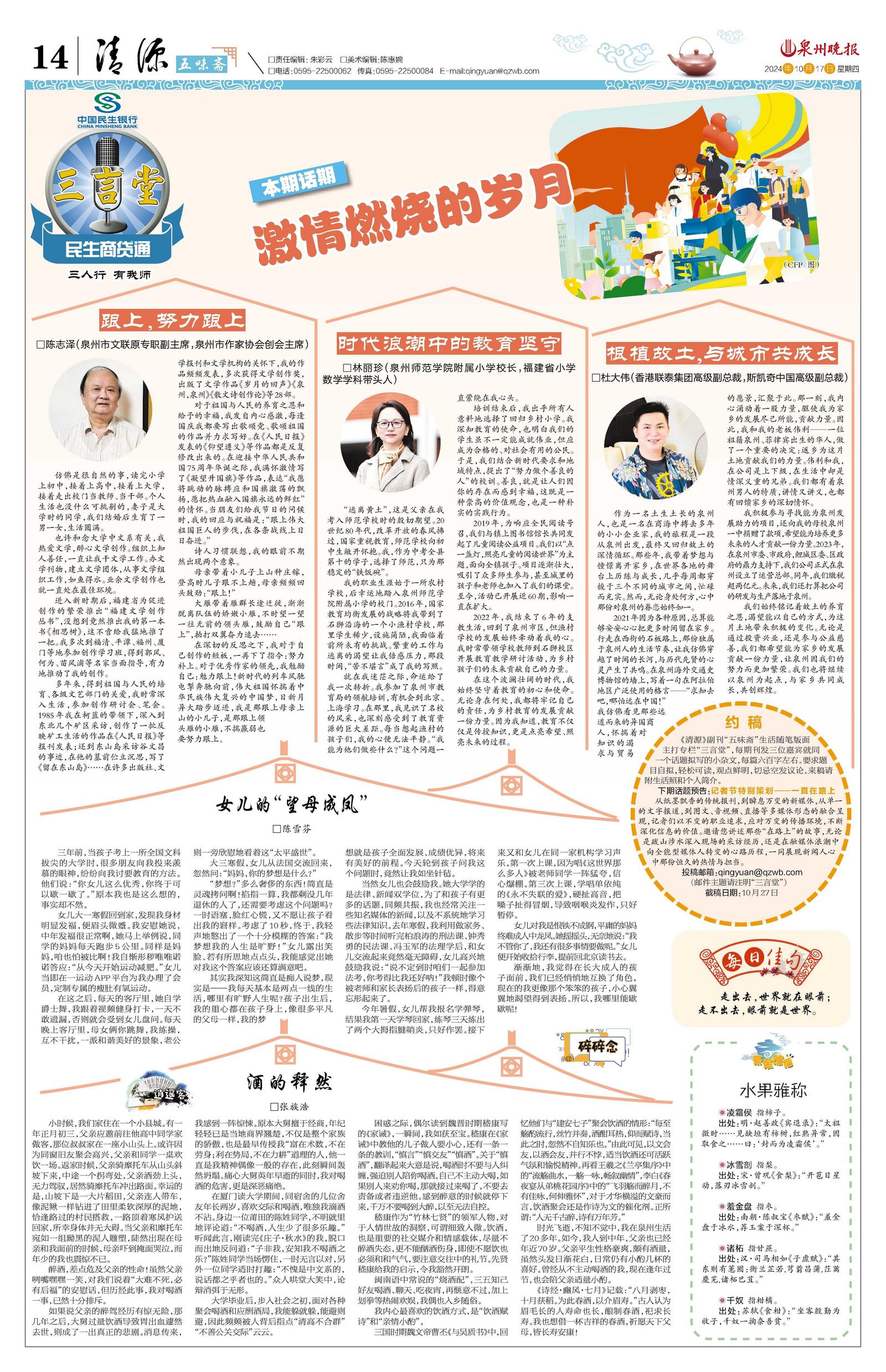小时候,我们家住在一个小县城。有一年正月初三,父亲应邀前往他高中同学家做客,那位叔叔家在一座小山头上。或许因为同窗旧友聚会高兴,父亲和同学一桌欢饮一场。返家时候,父亲骑摩托车从山头斜坡下来,中途一个拐弯处,父亲酒劲上头,无力驾驭,居然骑摩托车冲出路面。幸运的是,山坡下是一大片稻田,父亲连人带车,像泥鳅一样钻进了田里柔软深厚的泥地,恰逢路过的村民搭救,一路顶着寒风护送回家,所幸身体并无大碍。当父亲和摩托车宛如一组黝黑的泥人雕塑,陡然出现在母亲和我面前的时候,母亲吓到掩面哭泣,而年少的我也震惊不已。
醉酒,差点危及父亲的性命!虽然父亲咧嘴嘿嘿一笑,对我们说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安慰话,但历经此事,我对喝酒一事,已然十分排斥。
如果说父亲的醉驾经历有惊无险,那几年之后,大舅过量饮酒导致胃出血遽然去世,则成了一出真正的悲剧。消息传来,我感到一阵惊悚。原本大舅擅于经商,年纪轻轻已是当地商界翘楚,不仅是整个家族的骄傲,也是最早传授我“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局,不在力耕”道理的人,他一直是我精神偶像一般的存在,此刻瞬间轰然坍塌。痛心大舅英年早逝的同时,我对喝酒的危害,更是深恶痛绝。
在厦门读大学期间,同宿舍的几位舍友年长两岁,喜欢交际和喝酒,唯独我滴酒不沾。身边一位莆田的陈姓同学,不明就里地评论道:“不喝酒,人生少了很多乐趣。”听闻此言,刚读完《庄子·秋水》的我,脱口而出地反问道:“子非我,安知我不喝酒之乐?”陈姓同学当场愣住,一时无言以对,另外一位同学适时打趣:“不愧是中文系的,说话都之乎者也的。”众人哄堂大笑中,论辩消弭于无形。
大学毕业后,步入社会之初,面对各种聚会喝酒和应酬酒局,我能躲就躲,能避则避,因此频频被人背后指点“清高不合群”“不善公关交际”云云。
困惑之际,偶尔读到魏晋时期嵇康写的《家诫》,一瞬间,我如获至宝。嵇康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慎言”“慎交友”“慎酒”。关于“慎酒”,翻译起来大意是说,喝酒时不要与人纠缠,强迫别人陪你喝酒。自己不主动大喝,如果别人来劝你喝,那就接过来喝了,不要去责备或者违逆他。感到醉意的时候就停下来,千万不要喝到大醉,以至无法自控。
嵇康作为“竹林七贤”的领军人物,对于人情世故的洞察,可谓细致入微。饮酒,也是重要的社交媒介和情感载体,尽量不醉酒失态,更不能酗酒伤身,即使不愿饮也必须和和气气,要注意交往中的礼节。先贤嵇康给我的启示,令我豁然开朗。
闽南语中常说的“烧酒配”,三五知己好友喝酒、聊天、吃夜宵,再惬意不过,加上划拳等热闹欢娱,我偶也入乡随俗。
我内心最喜欢的饮酒方式,是“饮酒赋诗”和“亲情小酌”。
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与吴质书》中,回忆他们与“建安七子”聚会饮酒的情形:“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由此可见,以文会友,以酒会友,并行不悖,适当饮酒还可活跃气氛和愉悦精神。再看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流觞曲水,一觞一咏,畅叙幽情”,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的“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咏,何伸雅怀”,对于才华横溢的文豪而言,饮酒聚会还是作诗为文的催化剂。正所谓:“人无千古醉,诗有万年芳。”
时光飞逝,不知不觉中,我在泉州生活了20多年。如今,我人到中年,父亲也已经年近70岁。父亲平生性格豪爽,颇有酒量,虽然头发日渐花白,日常仍有小酌几杯的喜好。曾经从不主动喝酒的我,现在逢年过节,也会陪父亲适量小酌。
《诗经·豳风·七月》记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古人认为眉毛长的人寿命也长,酿制春酒,祀求长寿。我也想借一杯吉祥的春酒,祈愿天下父母,皆长寿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