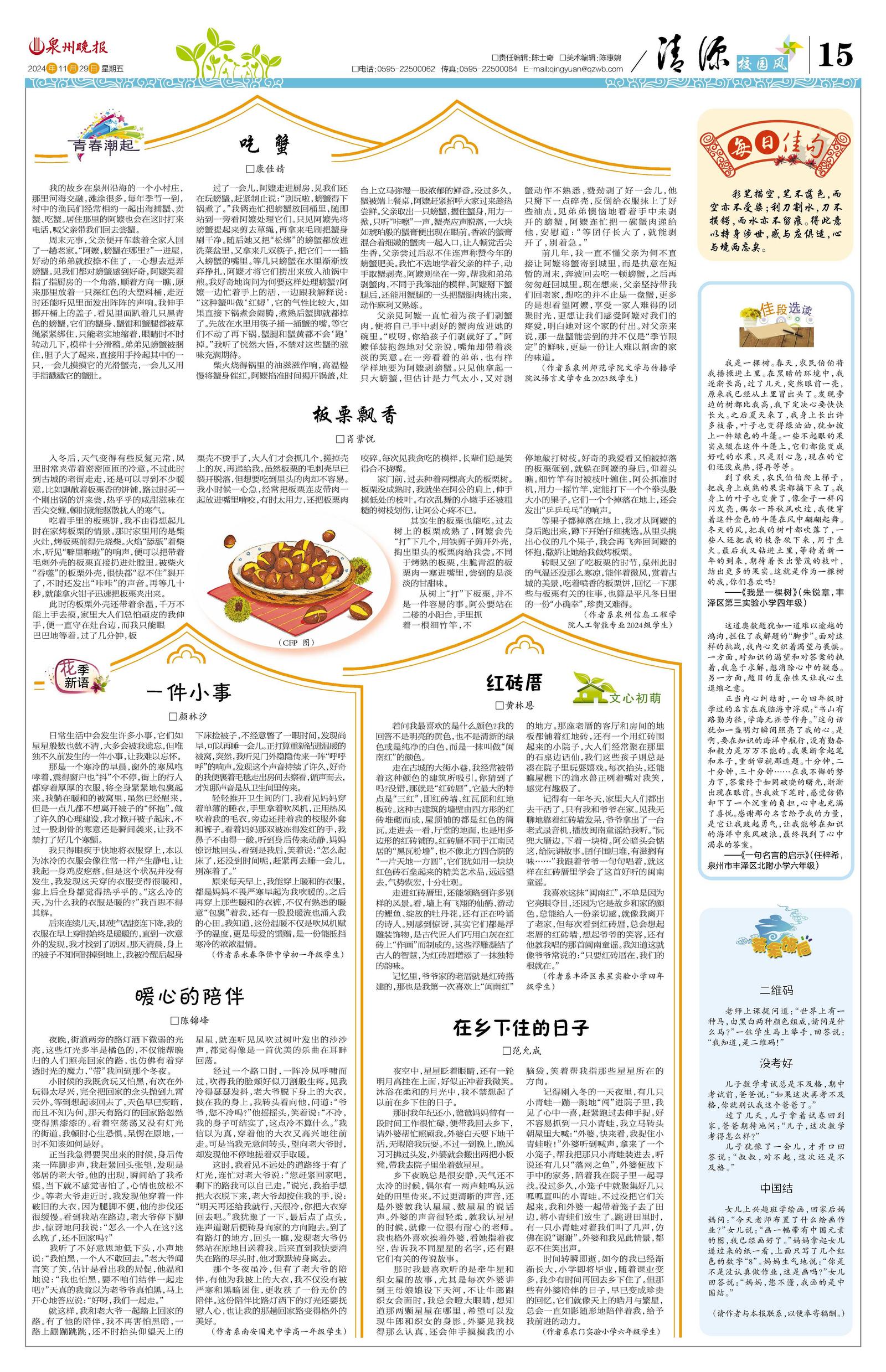我的故乡在泉州沿海的一个小村庄,那里河海交融,滩涂很多。每年季节一到,村中的渔民们经常相约一起出海捕蟹、卖蟹、吃蟹。居住那里的阿嬷也会在这时打来电话,喊父亲带我们回去尝蟹。
周末无事,父亲便开车载着全家人回了一趟老家。“阿嬷,螃蟹在哪里?”一进屋,好动的弟弟就按捺不住了,一心想去逗弄螃蟹。见我们都对螃蟹感到好奇,阿嬷笑着指了指厨房的一个角落,顺着方向一瞧,原来那里放着一只深红色的大塑料桶,走近时还能听见里面发出阵阵的声响。我伸手挪开桶上的盖子,看见里面趴着几只黑青色的螃蟹,它们的蟹身、蟹钳和蟹腿都被草绳紧紧绑住,只能老实地缩着,眼睛时不时转动几下,模样十分滑稽。弟弟见螃蟹被捆住,胆子大了起来,直接用手拎起其中的一只,一会儿摸摸它的光滑蟹壳,一会儿又用手指戳戳它的蟹肚。
过了一会儿,阿嬷走进厨房,见我们还在玩螃蟹,赶紧制止说:“别玩啦,螃蟹得下锅煮了。”我俩连忙把螃蟹放回桶里,随即站到一旁看阿嬷处理它们。只见阿嬷先将螃蟹提起来剪去草绳,再拿来毛刷把蟹身刷干净。随后她又把“松绑”的螃蟹都放进洗菜盆里,又拿来几双筷子,把它们一一插入螃蟹的嘴里。等几只螃蟹在水里渐渐放弃挣扎,阿嬷才将它们捞出来放入油锅中煎。我好奇地询问为何要这样处理螃蟹?阿嬷一边忙着手上的活,一边跟我解释说:“这种蟹叫做‘红蟳’,它的气性比较大,如果直接下锅煮会闹腾,煮熟后蟹脚就都掉了。先放在水里用筷子捅一捅蟹的嘴,等它们不动了再下锅,蟹腿和蟹黄都不会‘跑’掉。”我听了恍然大悟,不禁对这些蟹的滋味充满期待。
柴火烧得锅里的油滋滋作响,高温慢慢将蟹身催红,阿嬷掐准时间揭开锅盖,灶台上立马弥漫一股浓郁的鲜香。没过多久,蟹被端上餐桌,阿嬷赶紧招呼大家过来趁热尝鲜。父亲取出一只螃蟹,握住蟹身,用力一掀,只听“咔嚓”一声,蟹壳应声脱落,一大块如琥珀般的蟹膏便出现在眼前。香浓的蟹膏混合着细嫩的蟹肉一起入口,让人顿觉舌尖生香,父亲尝过后忍不住连声称赞今年的螃蟹肥美。我忙不迭地学着父亲的样子,动手取蟹剥壳。阿嬷则坐在一旁,帮我和弟弟剥蟹肉,不同于我笨拙的模样,阿嬷掰下蟹腿后,还能用蟹腿的一头把蟹腿肉挑出来,动作麻利又熟练。
父亲见阿嬷一直忙着为孩子们剥蟹肉,便将自己手中剥好的蟹肉放进她的碗里。“哎呀,你给孩子们剥就好了。”阿嬷佯装抱怨地对父亲说,嘴角却带着淡淡的笑意。在一旁看着的弟弟,也有样学样地要为阿嬷剥螃蟹。只见他拿起一只大螃蟹,但估计是力气太小,又对剥蟹动作不熟悉,费劲剥了好一会儿,他只掰下一点碎壳,反倒给衣服抹上了好些油点。见弟弟懊恼地看着手中未剥开的螃蟹,阿嬷连忙把一碗蟹肉递给他,安慰道:“等囝仔长大了,就能剥开了,别着急。”
前几年,我一直不懂父亲为何不直接让阿嬷将蟹寄到城里,而是执意在短暂的周末,奔波回去吃一顿螃蟹,之后再匆匆赶回城里。现在想来,父亲坚持带我们回老家,想吃的并不止是一盘蟹,更多的是想看望阿嬷,享受一家人难得的团聚时光,更想让我们感受阿嬷对我们的疼爱,明白她对这个家的付出。对父亲来说,那一盘蟹能尝到的并不仅是“季节限定”的鲜味,更是一份让人难以割舍的家的味道。
(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23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