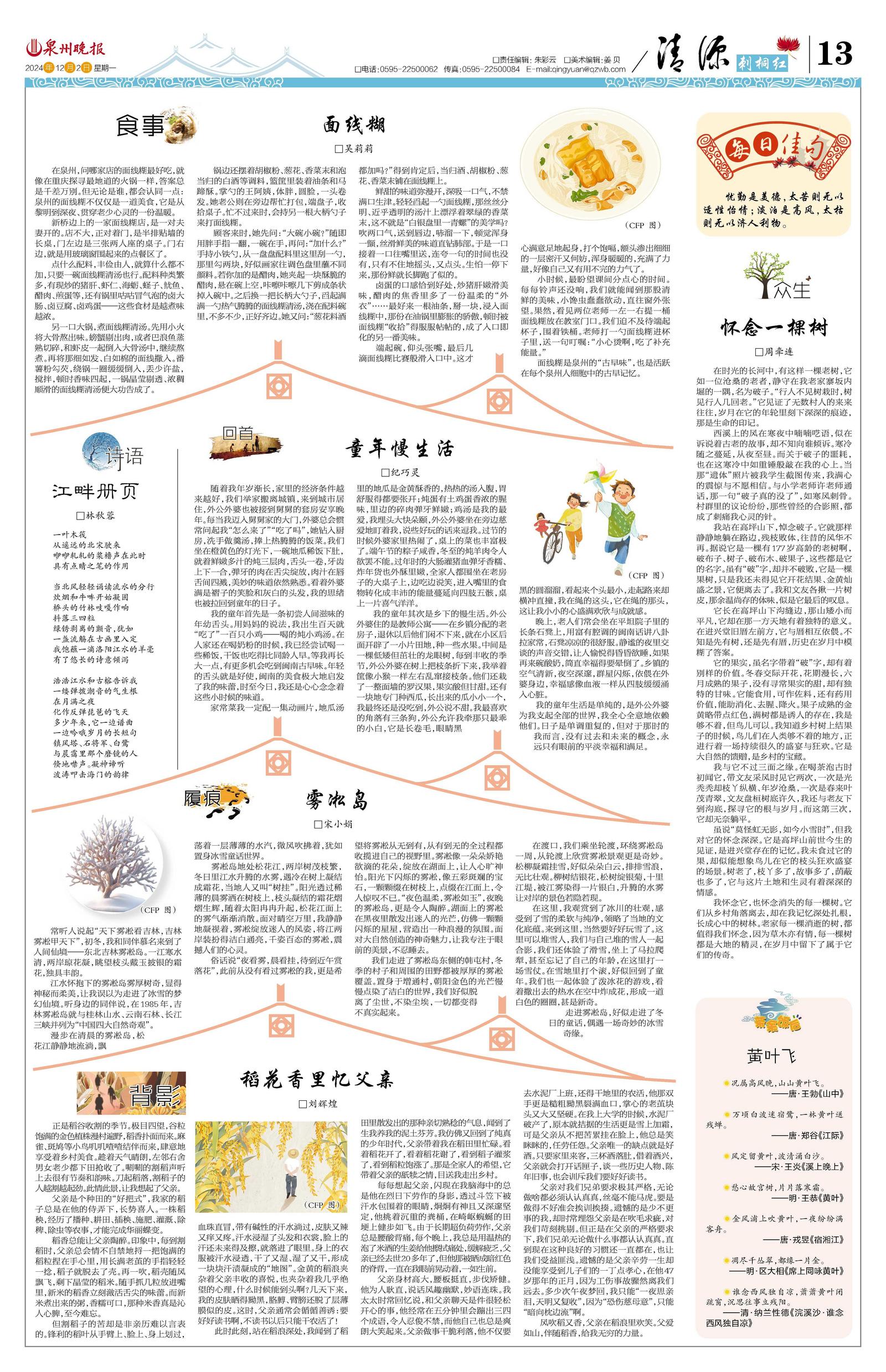正是稻谷收割的季节。极目四望,谷粒饱满的金色植株漫村遍野,稻香扑面而来。麻雀、斑鸠等小鸟叽叽喳喳结伴而来,肆意地享受着乡村美食。趁着天气晴朗,左邻右舍男女老少都下田抢收了。唰唰的割稻声听上去很有节奏和韵味。刀起稻落,割稻子的人越割越起劲。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父亲。
父亲是个种田的“好把式”,我家的稻子总是在他的侍弄下,长势喜人。一株稻秧,经历了播种、耕田、插秧、施肥、灌溉、除稗、除虫等农事,才能完成华丽蝶变。
稻香总能让父亲陶醉。印象中,每到割稻时,父亲总会情不自禁地捋一把饱满的稻粒捏在手心里,用长满老茧的手指轻轻一捻,稻子就脱去了壳。再一吹,稻壳随风飘飞,剩下晶莹的稻米。随手抓几粒放进嘴里,新米的稻香立刻激活舌尖的味蕾。而新米煮出来的粥,香糯可口,那种米香真是沁人心脾,至今难忘。
但割稻子的苦却是非亲历难以言表的。锋利的稻叶从手臂上、脸上、身上划过,血珠直冒,带有碱性的汗水淌过,皮肤又辣又痒又疼。汗水浸湿了头发和衣裳,脸上的汗还未来得及擦,就落进了眼里。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浸透,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形成一块块汗渍凝成的“地图”。金黄的稻浪夹杂着父亲丰收的喜悦,也夹杂着我几乎绝望的心理,什么时候能到头啊?几天下来,我的皮肤晒得黝黑,胳膊、臂膀还脱了层薄膜似的皮。这时,父亲通常会循循善诱:要好好读书啊,不读书以后只能干农活了!
此时此刻,站在稻浪深处,我闻到了稻田里散发出的那种亲切熟稔的气息,闻到了生我养我的泥土芬芳。我仿佛又回到了纯真的少年时代,父亲带着我在稻田里忙碌。看着稻花开了,看着稻花谢了,看到稻子灌浆了,看到稻粒饱涨了。那是全家人的希望,它带着父亲的舐犊之情,目送我走出乡村。
每每想起父亲,闪现在我脑海中的总是他在烈日下劳作的身影,透过斗笠下被汗水包围着的眼睛,炯炯有神且又深邃坚定,他挑着沉重的粪桶,在崎岖蜿蜒的田埂上健步如飞。由于长期超负荷劳作,父亲总是腰酸背痛,每个晚上,我总是用温热的泡了米酒的生姜给他擦拭痛处,缓解疲乏,父亲已经去世20多年了,但他那被晒成暗红色的脊背,一直在我眼前晃动着,一如生前。
父亲身材高大,腰板挺直,步伐矫健。他为人耿直,说话风趣幽默,妙语连珠。我太太时常回忆说,和父亲聊天是件很轻松开心的事,他经常在五分钟里会蹦出三四个成语,令人忍俊不禁,而他自己也总是爽朗大笑起来。父亲做事干脆利落,他不仅要去水泥厂上班,还得干地里的农活,他那双手更是糙粗黝黑裂满血口,掌心的老茧块头又大又坚硬。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水泥厂破产了,原本就拮据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可是父亲从不把苦累挂在脸上,他总是笑眯眯的,任劳任怨。父亲唯一的缺点就是好酒。只要家里来客,三杯酒落肚,借着酒兴,父亲就会打开话匣子,谈一些历史人物、陈年旧事,也会训斥我们要好好读书。
父亲对我们兄弟要求极其严格,无论做啥都必须认认真真,丝毫不能马虎。要是做得不好准会挨训挨揍。遗憾的是少不更事的我,却时常埋怨父亲是在吹毛求疵,对我们苛刻挑剔。但正是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我们兄弟无论做什么事都认认真真。直到现在这种良好的习惯还一直都在,也让我们受益匪浅。遗憾的是父亲辛劳一生却没能享受到儿子们的一丁点孝心,在他47岁那年的正月,因为工伤事故骤然离我们远去。多少次午夜梦回,我只能“一夜思亲泪,天明又复收”,因为“恐伤慈母意”,只能“暗向枕边流”啊。
风吹稻又香,父亲在稻浪里欢笑。父爱如山,伴随稻香,给我无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