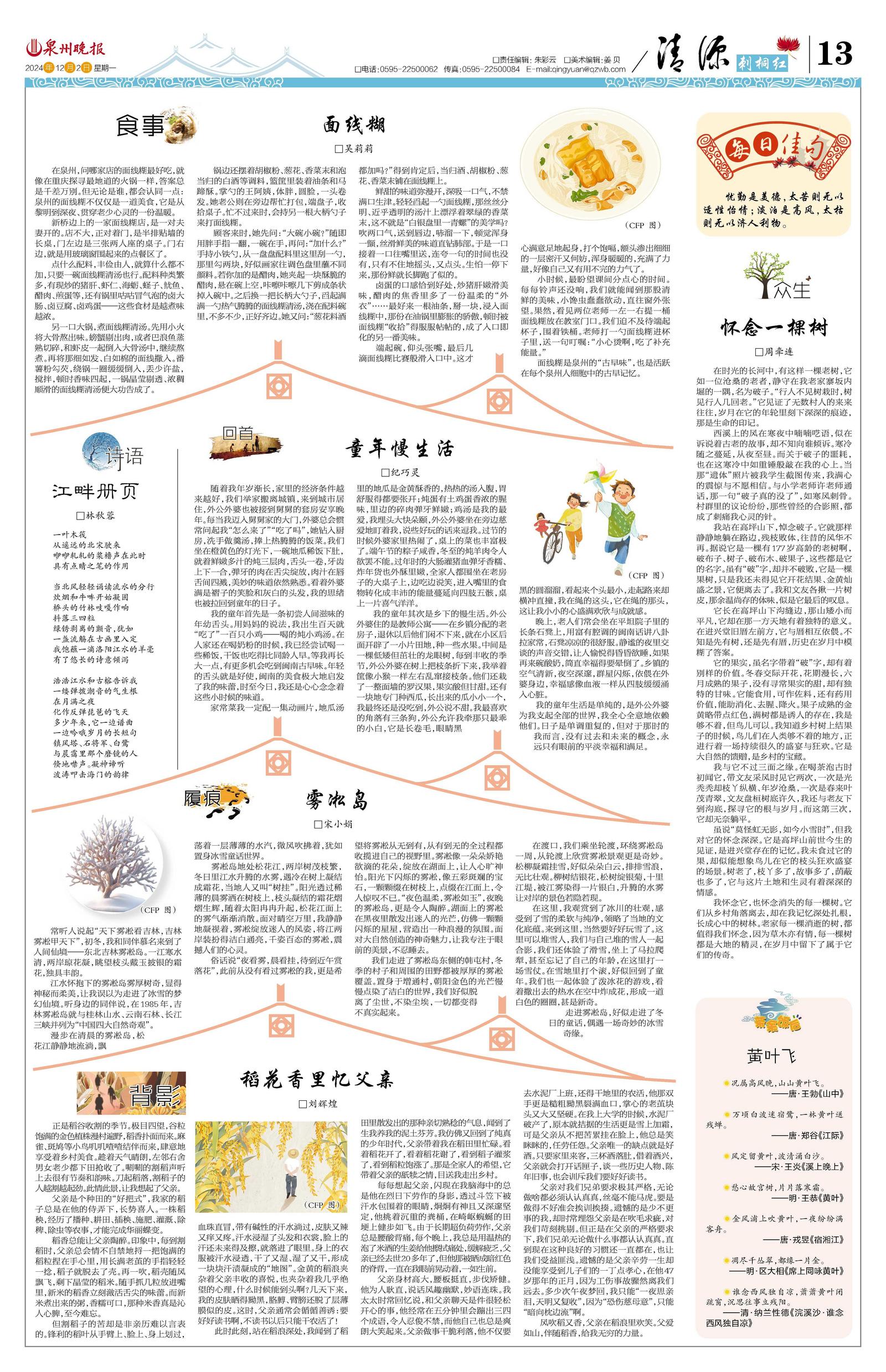随着我年岁渐长,家里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我们举家搬离城镇,来到城市居住,外公外婆也被接到舅舅的套房安享晚年。每当我迈入舅舅家的大门,外婆总会惯常问起我“怎么来了”“吃了吗”,她钻入厨房,洗手做羹汤,捧上热腾腾的饭菜。我们坐在橙黄色的灯光下,一碗地瓜稀饭下肚,就着鲜嫩多汁的炖三层肉,舌头一卷,牙齿上下一合,弹牙的肉在舌尖绽放,肉汁在唇舌间四溅,美妙的味道依然熟悉。看着外婆满是褶子的笑脸和灰白的头发,我的思绪也被拉回到童年的日子。
我的童年首先是一条初尝人间滋味的年幼舌头。用妈妈的说法,我出生百天就“吃了”一百只小鸡——喝的炖小鸡汤。在人家还在喝奶粉的时候,我已经尝试喝一些稀饭,干饭也吃得比同龄人早。等我再长大一点,有更多机会吃到闽南古早味。年轻的舌头就是好使,闽南的美食极大地启发了我的味蕾,时至今日,我还是心心念念着这些小时候的味道。
家常菜我一定配一集动画片,地瓜汤里的地瓜是金黄酥香的,热热的汤入腹,胃舒服得都要张开;炖蛋有土鸡蛋香浓的腥味,里边的碎肉弹牙鲜嫩;鸡汤是我的最爱,我埋头大快朵颐,外公外婆坐在旁边慈爱地盯着我,说些好玩的话来逗我。过节的时候外婆家里热闹了,桌上的菜也丰富极了。端午节的粽子咸香,冬至的炖羊肉令人欲罢不能。过年时的大肠灌猪血弹牙香糯、炸年货也外酥里嫩,全家人都围坐在老房子的大桌子上,边吃边说笑,进入嘴里的食物转化成丰沛的能量蔓延向四肢五骸,桌上一片喜气洋洋。
我的童年其次是乡下的慢生活。外公外婆住的是教师公寓——在乡镇分配的老房子,退休以后他们闲不下来,就在小区后面开辟了一小片田地,种一些水果。中间是一棵低矮但茁壮的龙眼树,每到丰收的季节,外公外婆在树上把枝条折下来,我举着筐像小猴一样左右乱窜接枝条。他们还栽了一整面墙的罗汉果,果实酸但甘甜。还有一块地专门种西瓜,长出来的瓜小小一个,我最终还是没吃到,外公说不甜。我最喜欢的角落有三条狗,外公允许我牵那只最乖的小白,它是长卷毛,眼睛黑黑的圆溜溜,看起来个头最小,走起路来却横冲直撞,我在绳的这头,它在绳的那头,这让我小小的心盛满欢欣与成就感。
晚上,老人们常会坐在平坦院子里的长条石凳上,用富有腔调的闽南话讲八卦拉家常,石凳凉凉的很舒服。静谧的夜里交谈的声音交错,让人愉悦得昏昏欲睡,如果再来碗酸奶,简直幸福得要晕倒了。乡镇的空气清新,夜空深邃,群星闪烁,依偎在外婆身边,幸福感像血液一样从四肢缓缓涌入心脏。
我的童年生活是单纯的,是外公外婆为我支起全部的世界,我全心全意地依赖他们。日子是单调重复的,但对于那时的我而言,没有过去和未来的概念,永远只有眼前的平淡幸福和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