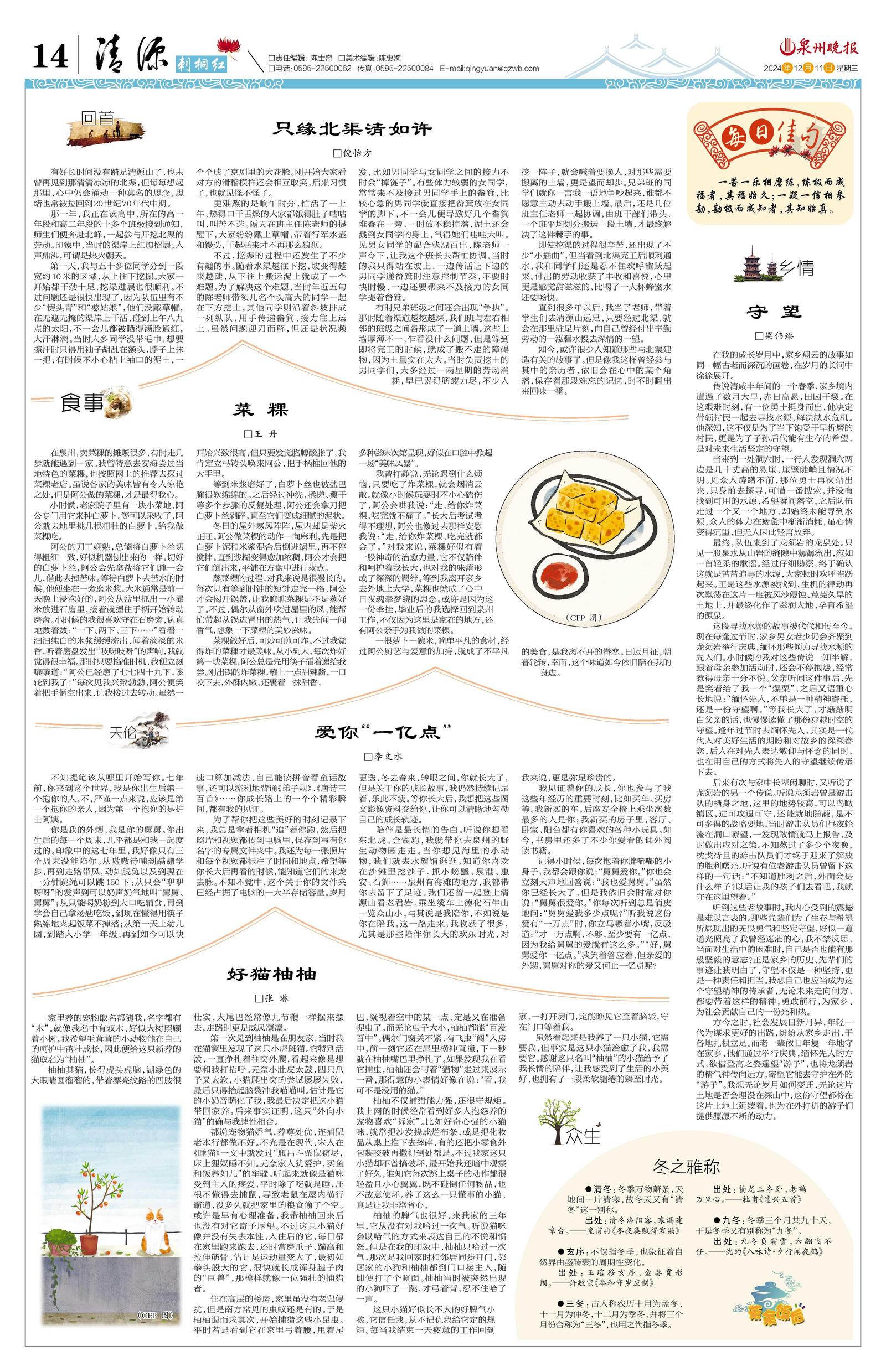在泉州,卖菜粿的摊贩很多,有时走几步就能遇到一家。我曾特意去安海尝过当地特色的菜粿,也按照网上的推荐去探过菜粿老店。虽说各家的美味皆有令人惊艳之处,但是阿公做的菜粿,才是最得我心。
小时候,老家院子里有一块小菜地,阿公专门用它来种白萝卜。等可以采收了,阿公就去地里挑几根粗壮的白萝卜,给我做菜粿吃。
阿公的刀工娴熟,总能将白萝卜丝切得粗细一致,好似机器刨出来的一样。切好的白萝卜丝,阿公会先拿盐将它们腌一会儿,借此去掉苦味。等待白萝卜去苦水的时候,他便坐在一旁磨米浆。大米通常是前一天晚上浸泡好的,阿公从盆里抓出一小撮米放进石磨里,接着就握住手柄开始转动磨盘。小时候的我很喜欢守在石磨旁,认真地数着数:“一下、两下、三下……”看着一汩汩纯白的米浆缓缓流出,闻着淡淡的米香,听着磨盘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我就觉得很幸福。那时只要掐准时机,我便立刻嚷嚷道:“阿公已经磨了七七四十九下,该轮到我了!”每次见我兴致勃勃,阿公便笑着把手柄空出来,让我接过去转动。虽然一开始兴致很高,但只要发觉胳膊酸胀了,我肯定立马转头唤来阿公,把手柄推回他的大手里。
等到米浆磨好了,白萝卜丝也被盐巴腌得软绵绵的。之后经过冲洗、揉搓、攥干等多个步骤的反复处理,阿公还会拿刀把白萝卜丝剁碎,直至它们变成细腻的泥状。
冬日的屋外寒风阵阵,屋内却是柴火正旺。阿公做菜粿的动作一向麻利,先是把白萝卜泥和米浆混合后倒进锅里,再不停搅拌。直到浆糊变得愈加浓稠,阿公才会把它们倒出来,平铺在方盘中进行蒸煮。
蒸菜粿的过程,对我来说是很漫长的。每次只有等到时钟的短针走完一格,阿公才会揭开锅盖,让我瞧瞧菜粿是不是蒸好了。不过,偶尔从窗外吹进屋里的风,能帮忙带起从锅边冒出的热气,让我先闻一闻香气,想象一下菜粿的美妙滋味。
菜粿做好后,可炒可煎可炸。不过我觉得炸的菜粿才最美味。从小到大,每次炸好第一块菜粿,阿公总是先用筷子插着递给我尝。刚出锅的炸菜粿,蘸上一点甜辣酱,一口咬下去,外酥内嫩,还裹着一抹甜香,多种滋味次第呈现,好似在口腔中掀起一场“美味风暴”。
我曾打趣说,无论遇到什么烦恼,只要吃了炸菜粿,就会烟消云散。就像小时候玩耍时不小心磕伤了,阿公会哄我说:“走,给你炸菜粿,吃完就不痛了。”长大后考试考得不理想,阿公也像过去那样安慰我说:“走,给你炸菜粿,吃完就都会了。”对我来说,菜粿好似有着一股神奇的治愈力量,它不仅陪伴和呵护着我长大,也对我的味蕾形成了深深的羁绊。等到我离开家乡去外地上大学,菜粿也就成了心中日夜魂牵梦绕的思念。或许是因为这一份牵挂,毕业后的我选择回到泉州工作,不仅因为这里是家在的地方,还有阿公亲手为我做的菜粿。
一根萝卜一碗米,简单平凡的食材,经过阿公厨艺与爱意的加持,就成了不平凡的美食,是我离不开的眷恋。日迈月征,朝暮轮转,幸而,这个味道如今依旧陪在我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