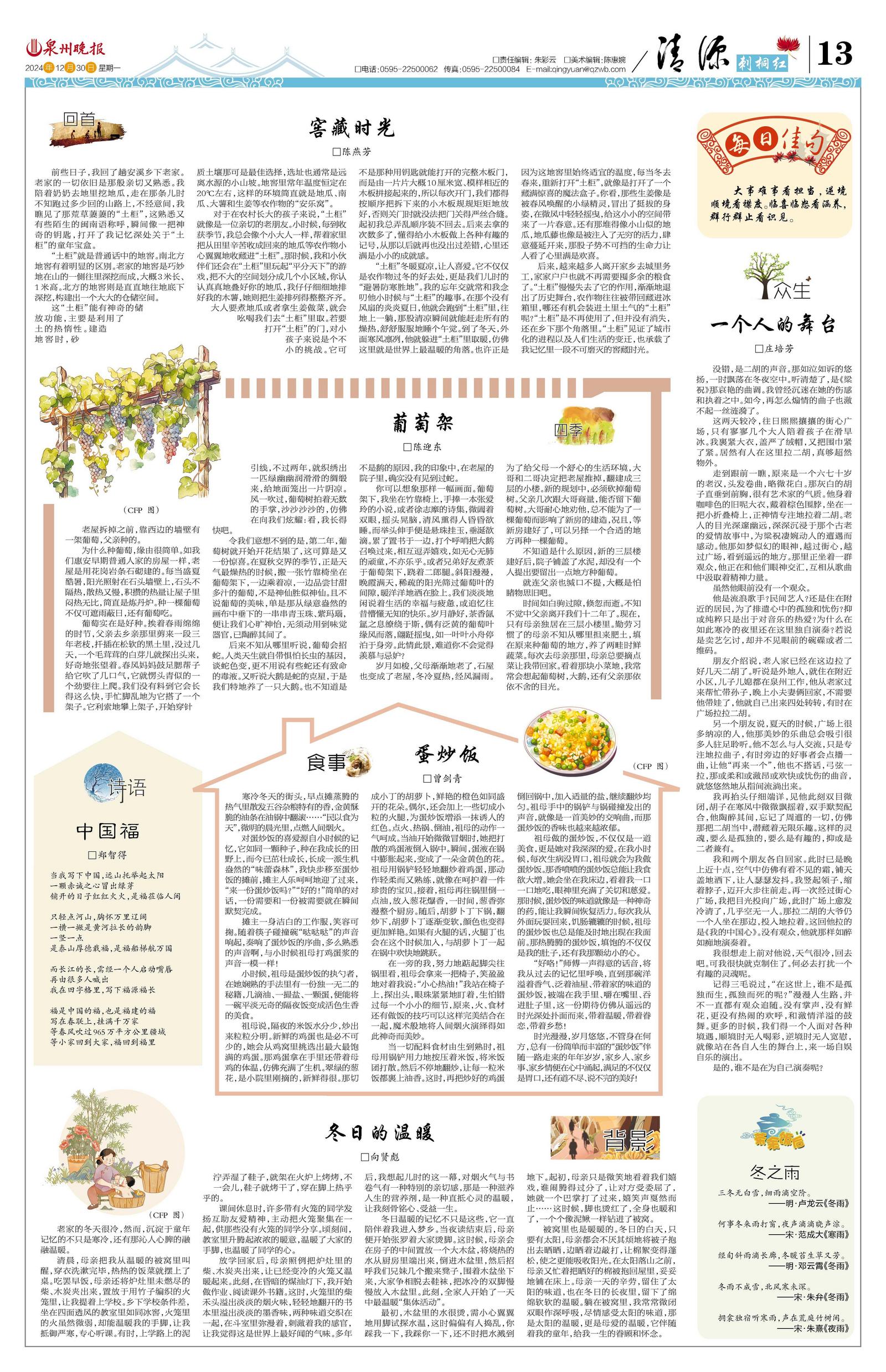老屋拆掉之前,靠西边的墙壁有一架葡萄,父亲种的。
为什么种葡萄,缘由很简单。如我们惠安早期普通人家的房屋一样,老屋是用花岗岩条石砌建的。每当盛夏酷暑,阳光照射在石头墙壁上,石头不隔热,散热又慢,积攒的热量让屋子里闷热无比,简直是炼丹炉。种一棵葡萄不仅可遮雨蔽日,还有葡萄吃。
葡萄实在是好种。挨着春雨绵绵的时节,父亲去乡亲那里剪来一段三年老枝,扦插在松软的黑土里,没过几天,一个毛茸茸的白芽儿就探出头来,好奇地张望着。春风妈妈鼓足腮帮子给它吹了几口气,它就愣头青似的一个劲要往上爬。我们没有料到它会长得这么快,手忙脚乱地为它搭了一个架子。它利索地攀上架子,开始穿针引线,不过两年,就织绣出一匹绿幽幽润滑滑的绸缎来,给地面笼出一片阴凉。风一吹过,葡萄树拍着无数的手掌,沙沙沙沙的,仿佛在向我们炫耀:看,我长得快吧。
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年,葡萄树就开始开花结果了,这可算是又一份惊喜。在夏秋交界的季节,正是天气最燥热的时候,搬一张竹靠椅坐在葡萄架下,一边乘着凉,一边品尝甘甜多汁的葡萄,不是神仙胜似神仙。且不说葡萄的美味,单是那从绿意盎然的画布中垂下的一串串青玉珠、紫玛瑙,便让我们心旷神怡,无须动用到味觉器官,已陶醉其间了。
后来不知从哪里听说,葡萄会招蛇。人类天生就自带惧怕长虫的基因,谈蛇色变,更不用说有些蛇还有致命的毒液。又听说大鹅是蛇的克星,于是我们特地养了一只大鹅。也不知道是不是鹅的原因,我的印象中,在老屋的院子里,确实没有见到过蛇。
你可以想象那样一幅画面。葡萄架下,我坐在竹靠椅上,手捧一本张爱玲的小说,或者徐志摩的诗集,微阖着双眼,摇头晃脑,清风熏得人昏昏欲睡。而举头伸手便是悬珠挂玉,垂涎欲滴。累了置书于一边,打个呼哨把大鹅召唤过来,相互逗弄嬉戏,如无心无肺的顽童,不亦乐乎。或者兄弟好友煮茶于葡萄架下,跷着二郎腿。斜阳漫漫,晚霞满天,稀疏的阳光筛过葡萄叶的间隙,暖洋洋地洒在脸上。我们淡淡地闲说着生活的幸福与疲惫,或追忆往昔懵懂无知的快乐。岁月静好,茶香氤氲之息缭绕于斯,偶有泛黄的葡萄叶缘风而落,翩跹摇曳,如一叶叶小舟停泊于身旁。此情此景,难道你不会觉得羡慕与忌妒?
岁月如梭,父母渐渐地老了,石屋也变成了老屋,冬冷夏热,经风漏雨。为了给父母一个舒心的生活环境,大哥和二哥决定把老屋推掉,翻建成三层的小楼。新的规划中,必须砍掉葡萄树。父亲几次跟大哥商量,能否留下葡萄树。大哥耐心地劝他,总不能为了一棵葡萄而影响了新房的建造,况且,等新房建好了,可以另择一个合适的地方再种一棵葡萄。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新的三层楼建好后,院子铺盖了水泥,却没有一个人提出要留出一点地方种葡萄。
就连父亲也缄口不提,大概是怕睹物思旧吧。
时间如白驹过隙,倏忽而逝。不知不觉中父亲离开我们十二年了。现在,只有母亲独居在三层小楼里。勤劳习惯了的母亲不知从哪里担来肥土,填在原来种葡萄的地方,养了两畦时鲜蔬菜。每次去母亲那里,母亲总要摘点菜让我带回家。看着那块小菜地,我常常会想起葡萄树,大鹅,还有父亲那依依不舍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