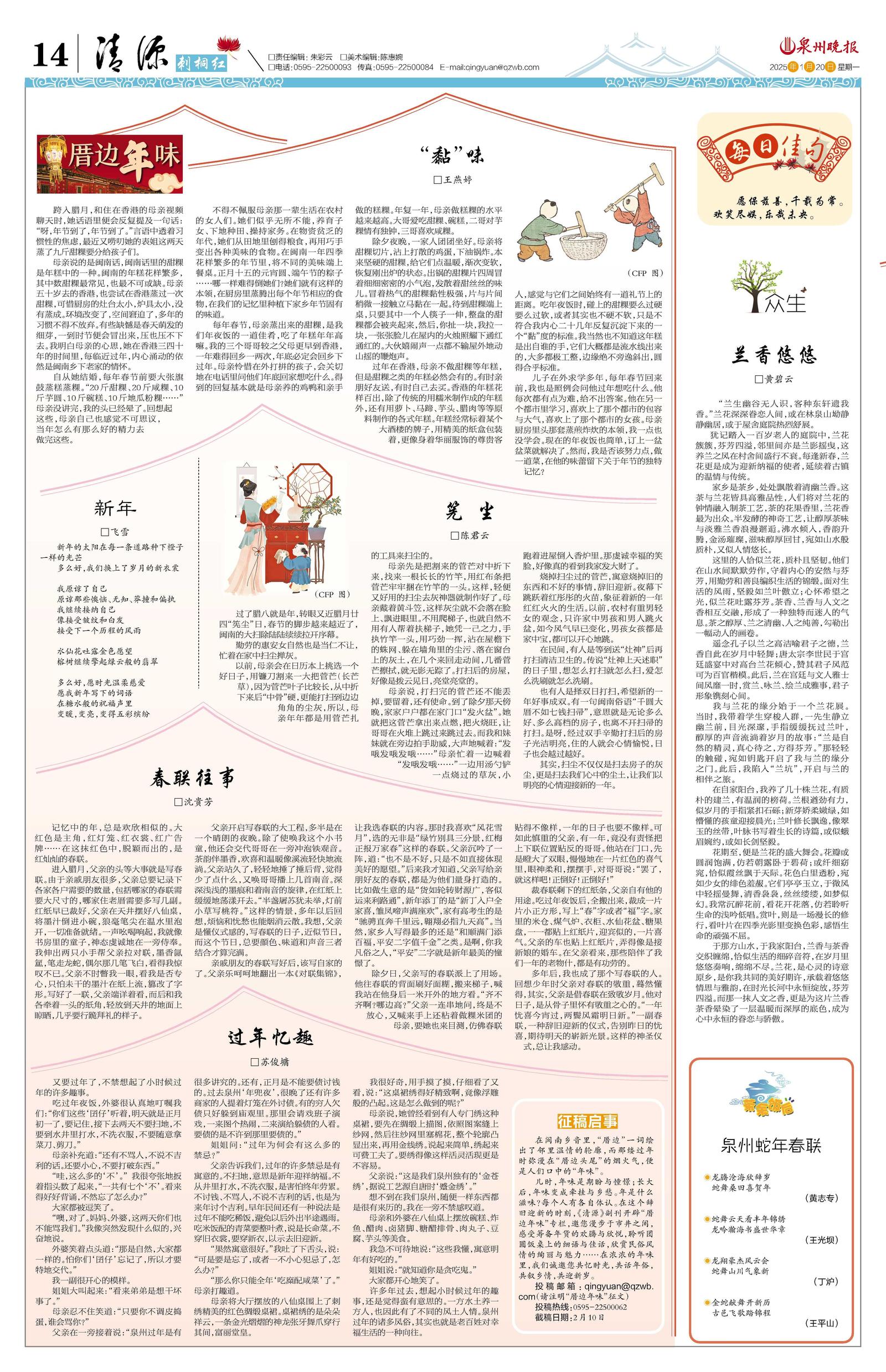跨入腊月,和住在香港的母亲视频聊天时,她话语里便会反复提及一句话:“呀,年节到了,年节到了。”言语中透着习惯性的焦虑,最近又唠叨她的表姐这两天蒸了九斤甜粿要分给孩子们。
母亲说的是闽南话,闽南话里的甜粿是年糕中的一种。闽南的年糕花样繁多,其中数甜粿最常见,也最不可或缺。母亲五十岁去的香港,也尝试在香港蒸过一次甜粿,可惜厨房的灶台太小,炉具太小,没有蒸成。环境改变了,空间窘迫了,多年的习惯不得不放弃。有些缺憾是春天萌发的细芽,一到时节便会冒出来,压也压不下去。我明白母亲的心思,她在香港三四十年的时间里,每临近过年,内心涌动的依然是闽南乡下老家的情怀。
自从她结婚,每年春节前要大张旗鼓蒸糕蒸粿。“20斤甜粿、20斤咸粿、10斤芋圆、10斤碗糕、10斤地瓜粉粿……”母亲没讲完,我的头已经晕了。回想起这些,母亲自己也感觉不可思议,当年怎么有那么好的精力去做完这些。
不得不佩服母亲那一辈生活在农村的女人们。她们似乎无所不能,养育子女、下地种田、操持家务。在物资贫乏的年代,她们从田地里刨得粮食,再用巧手变出各种美味的食物。在闽南一年四季花样繁多的年节里,将不同的美味端上餐桌。正月十五的元宵圆、端午节的粽子……哪一样难得倒她们?她们就有这样的本领,在厨房里蒸腾出每个年节相应的食物,在我们的记忆里种植下家乡年节固有的味道。
每年春节,母亲蒸出来的甜粿,是我们年夜饭的一道佳肴,吃了年糕年年高嘛。我的三个哥哥较之父母更早到香港,一年难得回乡一两次,年底必定会回乡下过年。母亲怜惜在外打拼的孩子,会关切地在电话里问他们年底回家想吃什么。得到的回复基本就是母亲养的鸡鸭和亲手做的糕粿。年复一年,母亲做糕粿的水平越来越高。大哥爱吃甜粿、碗糕,二哥对芋粿情有独钟,三哥喜欢咸粿。
除夕夜晚,一家人团团坐好。母亲将甜粿切片,沾上打散的鸡蛋,下油锅炸。本来坚硬的甜粿,给它们点温暖,渐次变软,恢复刚出炉的状态。出锅的甜粿片四周冒着细细密密的小气泡,发散着甜丝丝的味儿。冒着热气的甜粿黏性极强,片与片间稍微一接触立马黏在一起。待到甜粿端上桌,只要其中一个人筷子一伸,整盘的甜粿都会被夹起来,然后,你扯一块,我拉一块,一张张脸儿在屋内的火烛照耀下通红通红的。大伙嬉闹声一点都不输屋外地动山摇的鞭炮声。
过年在香港,母亲不做甜粿等年糕,但是甜粿之类的年糕必然会有的。有时亲朋好友送,有时自己去买。香港的年糕花样百出,除了传统的用糯米制作成的年糕外,还有用萝卜、马蹄、芋头、腊肉等等原料制作的各式年糕。年糕经常标着某个大酒楼的牌子,用精美的纸盒包装着,更像身着华丽服饰的尊贵客人,感觉与它们之间始终有一道礼节上的距离。 吃年夜饭时,碰上的甜粿要么过硬要么过软,或者其实也不硬不软,只是不符合我内心二十几年反复沉淀下来的一个“黏”度的标准。我当然也不知道这年糕是出自谁的手,它们大概都是流水线出来的,大多都极工整,边缘绝不旁逸斜出,圆得合乎标准。
儿子在外求学多年,每年春节回来前,我也是照例会问他过年想吃什么。他每次都有点为难,给不出答案。他在另一个都市里学习,喜欢上了那个都市的包容与大气,喜欢上了那个都市的女孩。母亲厨房里头那套蒸煎炸炊的本领,我一点也没学会。现在的年夜饭也简单,订上一盆盆菜就解决了。然而,我是否该努力点,做一道菜,在他的味蕾留下关于年节的独特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