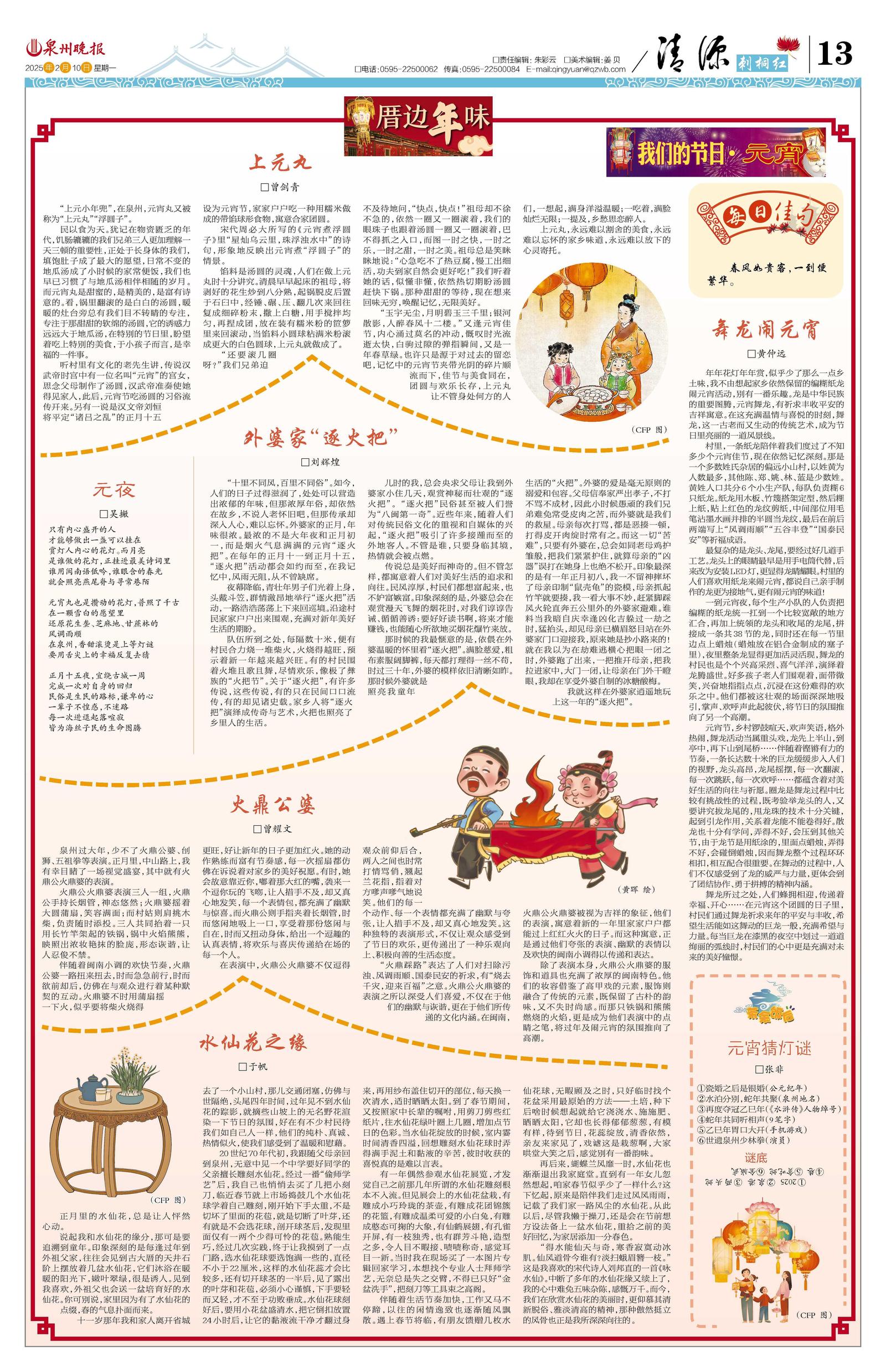“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如今,人们的日子过得滋润了,处处可以营造出浓郁的年味,但那浓厚年俗,却依然在故乡,不说人老怀旧吧,但那传承却深入人心,难以忘怀。外婆家的正月,年味很浓。最浓的不是大年夜和正月初一,而是烟火气息满满的元宵“逐火把”。在每年的正月十一到正月十五,“逐火把”活动都会如约而至,在我记忆中,风雨无阻,从不曾缺席。
夜幕降临,青壮年男子们光着上身,头戴斗笠,群情激昂地举行“逐火把”活动,一路浩浩荡荡上下来回巡境。沿途村民家家户户出来围观,充满对新年美好生活的期盼。
队伍所到之处,每隔数十米,便有村民合力烧一堆柴火,火烧得越旺,预示着新一年越来越兴旺。有的村民围着火堆且歌且舞,尽情欢乐,像极了彝族的“火把节”。关于“逐火把”,有许多传说,这些传说,有的只在民间口口流传,有的却见诸史载。家乡人将“逐火把”演绎成传奇与艺术,火把也照亮了乡里人的生活。
儿时的我,总会央求父母让我到外婆家小住几天,观赏神秘而壮观的“逐火把”。 “逐火把”民俗甚至被人们誉为“八闽第一奇”。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视和自媒体的兴起,“逐火把”吸引了许多接踵而至的外地客人。不管是谁,只要身临其境,热情就会被点燃。
传说总是美好而神奇的。但不管怎样,都寓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民风淳厚,村民们都想富起来,也不妒富嫉富。印象深刻的是,外婆总会在观赏漫天飞舞的烟花时,对我们谆谆告诫、循循善诱:要好好读书啊,将来才能赚钱,也能随心所欲地买烟花爆竹来放。
那时候的我最惬意的是,依偎在外婆温暖的怀里看“逐火把”。满脸慈爱,粗布素服阔脚裤,每天都打理得一丝不苟,时过三十年,外婆的模样依旧清晰如昨。那时候外婆就是照亮我童年生活的“火把”。外婆的爱是毫无原则的溺爱和包容。父母信奉家严出孝子,不打不骂不成材,因此小时候愚顽的我们兄弟难免常受皮肉之苦,而外婆就是我们的救星。母亲每次打骂,都是恶揍一顿,打得皮开肉绽时常有之。而这一切“苦难”,只要有外婆在,总会如同老母鸡护雏般,把我们紧紧护住,就算母亲的“凶器”误打在她身上也绝不松开。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正月初八,我一不留神摔坏了母亲印制“鼠壳龟”的瓷模,母亲抓起竹竿就要揍,我一看大事不妙,赶紧脚踩风火轮直奔五公里外的外婆家避难。谁料当我暗自庆幸逢凶化吉躲过一劫之时,猛抬头,却见母亲已横眉怒目站在外婆家门口迎接我,原来她是抄小路来的!就在我以为在劫难逃横心把眼一闭之时,外婆跑了出来,一把推开母亲,把我拉进家中,大门一闭,让母亲在门外干瞪眼,我却在享受外婆自制的冰糖酸梅。
我就这样在外婆家逍遥地玩上这一年的“逐火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