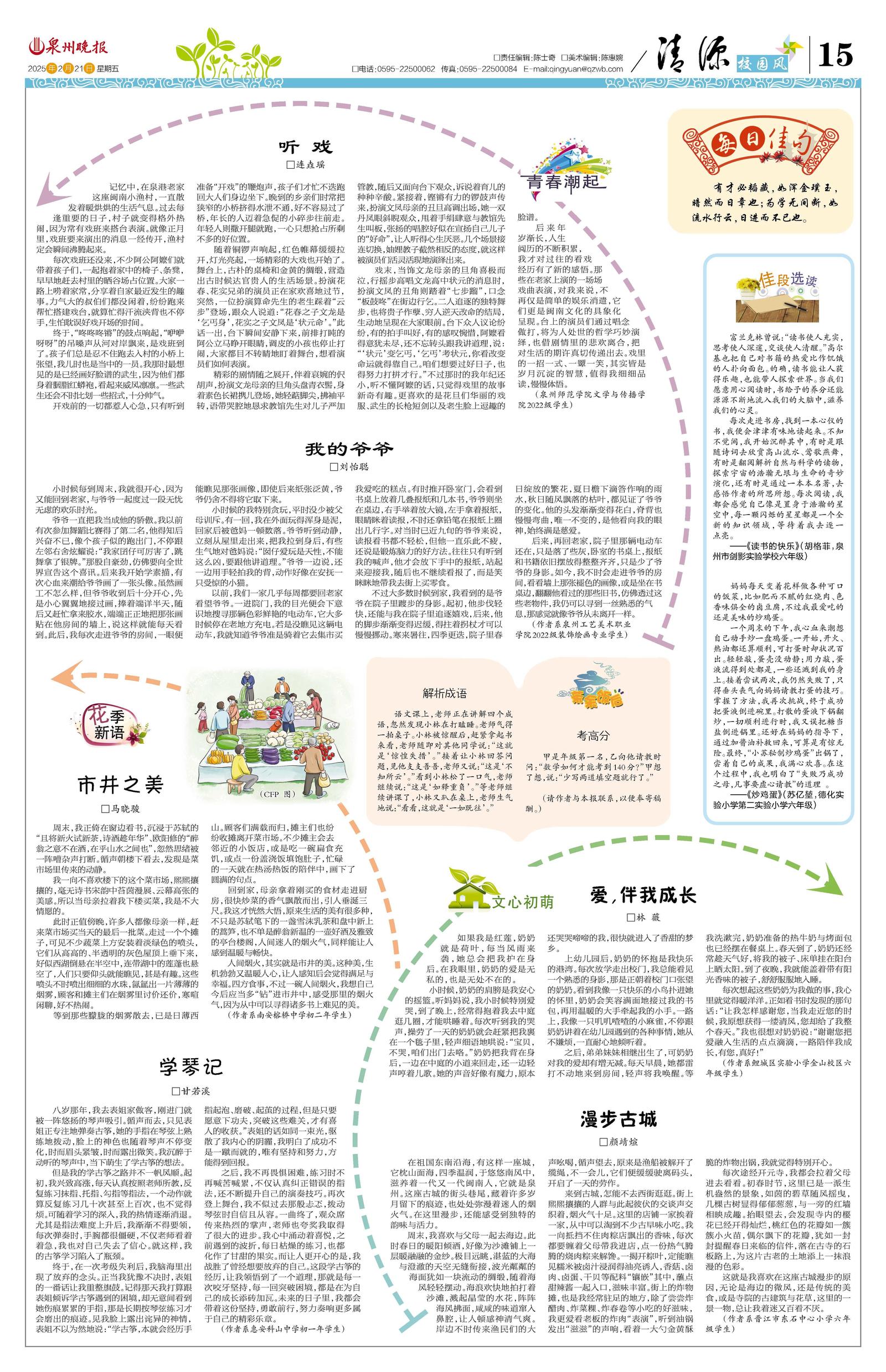记忆中,在泉港老家这座闽南小渔村,一直散发着暖烘烘的生活气息。过去每逢重要的日子,村子就变得格外热闹,因为常有戏班来搭台表演。就像正月里,戏班要来演出的消息一经传开,渔村定会瞬间沸腾起来。
每次戏班还没来,不少阿公阿嬷们就带着孩子们,一起抱着家中的椅子、条凳,早早地赶去村里的晒谷场占位置。大家一路上唠着家常,分享着自家最近发生的趣事。力气大的叔伯们都没闲着,纷纷跑来帮忙搭建戏台,就算忙得汗流浃背也不停手,生怕耽误好戏开场的时间。
终于,“咚咚咚锵”的鼓点响起,“咿咿呀呀”的吊嗓声从河对岸飘来,是戏班到了。孩子们总是忍不住跑去入村的小桥上张望,我儿时也是当中的一员。我那时最想见的是已经画好脸谱的武生,因为他们都身着胭脂红蟒袍,看起来威风凛凛。一些武生还会不时比划一些招式,十分帅气。
开戏前的一切都惹人心急,只有听到准备“开戏”的鞭炮声,孩子们才忙不迭跑回大人们身边坐下。晚到的乡亲们时常把狭窄的小桥挤得水泄不通,好不容易过了桥,年长的人迈着急促的小碎步往前走。年轻人则撒开腿就跑,一心只想抢占所剩不多的好位置。
随着铜锣声响起,红色帷幕缓缓拉开,灯光亮起,一场精彩的大戏也开始了。舞台上,古朴的桌椅和金黄的绸缎,营造出古时候达官贵人的生活场景。扮演花春、花实兄弟的演员正在家欢喜地过节,突然,一位扮演算命先生的老生踩着“云步”登场,跟众人说道:“花春之子文龙是‘乞丐身’,花实之子文凤是‘状元命’。”此话一出,台下瞬间安静下来,前排打盹的阿公立马睁开眼睛,调皮的小孩也停止打闹,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想看演员们如何表演。
精彩的剧情随之展开,伴着哀婉的伬胡声,扮演文龙母亲的旦角头盘青衣髻,身着素色长裙携儿登场,她轻踮脚尖,拂袖平转,语带哭腔地恳求教馆先生对儿子严加管教,随后又面向台下观众,诉说着育儿的种种辛酸。紧接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传来,扮演文凤母亲的丑旦高调出场,她一双丹凤眼斜睨观众,甩着手绢肆意与教馆先生叫板,张扬的唱腔好似在宣扬自己儿子的“好命”,让人听得心生厌恶。几个场景接连切换,妯娌教子截然相反的态度,就这样被演员们活灵活现地演绎出来。
戏末,当饰文龙母亲的旦角喜极而泣,行摇步高唱文龙高中状元的消息时,扮演文凤的丑角则踏着“七步蹓”,口念“板鼓咚”在街边行乞。二人追逐的独特舞步,也将贵子作孽、穷人逆天改命的结局,生动地呈现在大家眼前。台下众人议论纷纷,有的拍手叫好,有的感叹惋惜,阿嬷看得意犹未尽,还不忘转头跟我讲道理,说:“‘状元’变乞丐,‘乞丐’考状元,你看改变命运就得靠自己。咱们想要过好日子,也得努力打拼才行。”不过那时的我年纪还小,听不懂阿嬷的话,只觉得戏里的故事新奇有趣。更喜欢的是花旦们华丽的戏服、武生的长枪短剑以及老生脸上逗趣的脸谱。
后来年岁渐长,人生阅历的不断积累,我才对过往的看戏经历有了新的感悟。那些在老家上演的一场场戏曲表演,对我来说,不再仅是简单的娱乐消遣,它们更是闽南文化的具象化呈现。台上的演员们通过唱念做打,将为人处世的哲学巧妙演绎,也借剧情里的悲欢离合,把对生活的期许真切传递出去。戏里的一招一式、一颦一笑,其实皆是岁月沉淀的智慧,值得我细细品读,慢慢体悟。
(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2022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