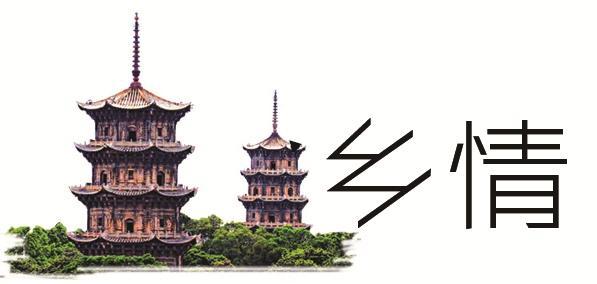我的老家最南边,本地人称它为“瓦窑垵”。所谓的“垵”,是指山坳,也就是小平地上盖着一排土墙房子。这些房子两面通风,旁边还搭建一个会冒烟的大瓦窑,里面可以烧制盖房子用的瓦片和砖块。
我儿时第一次去瓦窑垵,是在一个春日中午。一走进屋,就看到父亲与几位叔伯都光着膀子,身边放着一大堆泥土。只见父亲麻利地抓起一块泥土,用力甩在一个木框上,随后再拿工具刮去框外的泥土,一片瓦坯就算成型了。做好的瓦坯,层层叠叠地堆在一起,犹如高耸的山峰。此时位于斜坡上的瓦窑,炉火烧得正旺,父亲见我来了,赶紧递过来一把松枝,叫我拿去放进炉膛里烧,说是“添火”。除了帮父亲跑腿,我那时还跟在大人们身后学“印瓦”。有时泥巴涂得满脸,还惹得父亲笑弯了腰。
第二年,父亲去外地当代课老师,一家人便跟着他离开了家乡。直到我上小学六年级,老家盖的新厝要“下落”,需要准备一些砖瓦,父亲才带着全家人回了一趟老家。砖瓦出窑的那天,我高兴地跟着大人们一起扛着扁担赶去瓦窑垵。之所以干劲十足,是因为父亲说新厝建好,我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当时的我个子矮,单肩无法长时间挑着装满砖瓦的扁担,只得一路不停地“换肩”。谁知一不小心,半途摔了一跤,担子里的砖头掉落四散,吓得我顿时顾不上疼,赶忙跑去把它们一一捡回来。还好那些砖瓦的质量过硬,没有磕坏或破损,让我松了一口气。
那天回到家,听祖父说起,我才知整个村子盖房子用的砖瓦,都是在瓦窑垵烧制的。我好奇那个瓦窑是何时建的?祖父回想了半天,最后只说他小时候就有了。即使后来不少房子都翻新改建,但直到现在,村里仍保留着三十多座瓦房,使用的砖瓦皆是产自瓦窑垵。这些房子大部分是“十间张”的大厝,当中一些还带着“护厝”,每次置身其中,总感觉时光未曾流逝。
我每次跟外地朋友聊起老家,都形容那是一座“建在瓦上”的村庄。从村口远远望去,屋顶的瓦片一簇挨着一簇,与绿水青山相映成趣。瓦片的颜色还会跟随四季不断“变化”,比如迎来春夏,老厝前的大树开满花,偶尔飘落的花叶,会将瓦片点缀得色彩缤纷。进入秋冬,地瓜片、柿饼、豆角等铺在屋顶的瓦片上,又犹如一幅丰收的画卷徐徐展开。有时气温骤降,瓦片上还会结出薄薄的白霜,看起来又是别样的韵味。
不过,我更喜欢雨中的瓦片。有时春雨来袭,我便搬一把凳子坐在天井的走廊上赏雨。雨点敲打瓦片发出的沙沙声,好似春蚕啃食桑叶的声音,十分有趣。汇聚的雨水顺着瓦楞流下,一些从滴水兽嘴里吐出,形成一条条银亮的雨线,打在深井埕中,还会溅起小小的水花。这样雨雾朦胧的景象,每每回想,我就觉得心情格外愉悦。
我想,很多人心中的家园,就是这样一座用砖瓦搭建的老房子。屋顶天天升起袅袅的炊烟,厅堂大梁下筑有鸟巢,燕子进进出出,屋檐下还挂着晒干的菜籽,墙角放着锄头、扁担、畚箕等农具。每次走到大门口,还能看到门上贴着一副对联,左边写着“福寿”,右边写着“康宁”。这样的老厝,是温暖的归巢,是无论岁月如何流转、脚步迈向何方,都萦绕在游子们心中的羁绊。就像对我来说,老厝的一砖一瓦总像在诉说着家的故事,它们静静伫立在故乡的土地上,让我在漂泊的时光里,永远有处可依,有根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