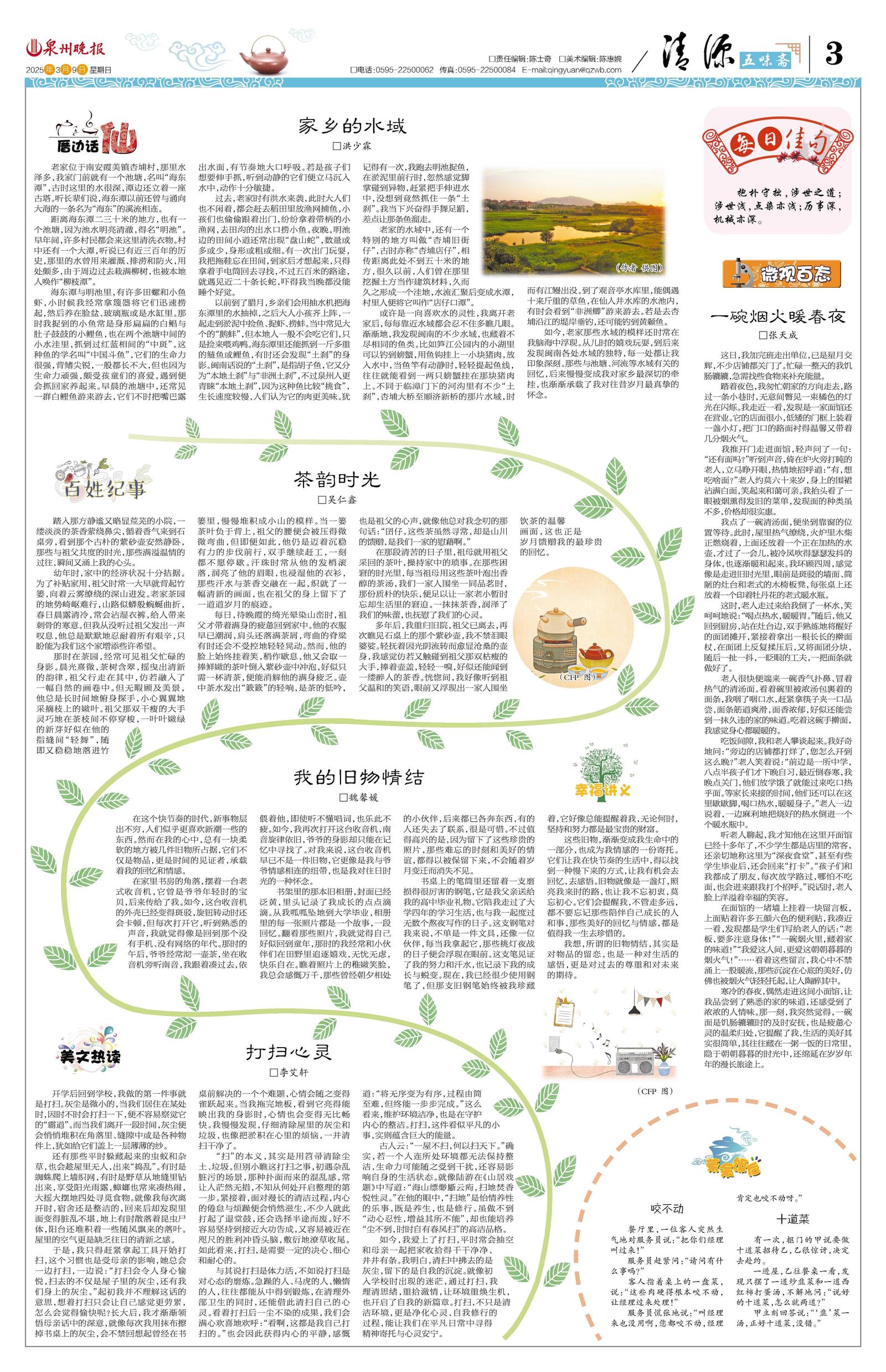□洪少霖
老家位于南安霞美镇杏埔村,那里水泽多,我家门前就有一个池塘,名叫“海东潭”,古时这里的水很深,潭边还立着一座古塔。听长辈们说,海东潭以前还曾与通向大海的一条名为“海东”的溪流相连。
距离海东潭二三十米的地方,也有一个池塘,因为池水明亮清澈,得名“明池”。早年间,许多村民都会来这里清洗衣物。村中还有一个大潭,听说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那里的水曾用来灌溉、排涝和防火,用处颇多,由于周边过去栽满柳树,也被本地人唤作“柳枝潭”。
海东潭与明池里,有许多田螺和小鱼虾,小时候我经常拿篾器将它们迅速捞起,然后养在脸盆、玻璃瓶或是水缸里。那时我捉到的小鱼常是身形扁扁的白鲳与肚子鼓鼓的小鲤鱼,也在两个池塘中间的小水洼里,抓到过红蓝相间的“中斑”。这种鱼的学名叫“中国斗鱼”,它们的生命力很强,背鳍尖锐,一般都长不大,但也因为生命力顽强,颇受孩童们的喜爱,遇到便会抓回家养起来。早晨的池塘中,还常见一群白鲤鱼游来游去,它们不时把嘴巴露出水面,有节奏地大口呼吸。若是孩子们想要伸手抓,听到动静的它们便立马沉入水中,动作十分敏捷。
过去,老家时有洪水来袭,此时大人们也不闲着,都会赶去稻田里放渔网捕鱼,小孩们也偷偷跟着出门,纷纷拿着带柄的小渔网,去田沟的出水口捞小鱼。夜晚,明池边的田间小道还常出现“盘山蛇”,数量或多或少,身形或粗或细。有一次出门玩耍,我把拖鞋忘在田间,到家后才想起来,只得拿着手电筒回去寻找,不过五百米的路途,就遇见近二十条长蛇,吓得我当晚都没能睡个好觉。
以前到了腊月,乡亲们会用抽水机把海东潭里的水抽掉,之后大人小孩齐上阵,一起走到淤泥中捡鱼、捉虾、捞蚌。当中常见大个的“鹅蚌”,但本地人一般不会吃它们,只是捡来喂鸡鸭。海东潭里还能抓到一斤多重的鲢鱼或鲤鱼,有时还会发现“土刹”的身影。闽南话说的“土刹”,是指胡子鱼,它又分为“本地土刹”与“非洲土刹”,不过泉州人更青睐“本地土刹”,因为这种鱼比较“挑食”,生长速度较慢,人们认为它的肉更美味。犹记得有一次,我跑去明池捉鱼,在淤泥里前行时,忽然感觉脚掌碰到异物,赶紧把手伸进水中,没想到竟然抓住一条“土刹”。我当下兴奋得手舞足蹈,差点让那条鱼溜走。
老家的水域中,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叫做“杏埔旧街仔”,古时亦称“杏埔店仔”,相传距离此处不到五十米的地方,很久以前,人们曾在那里挖掘土方当作建筑材料,久而久之形成一个洼地,水流汇聚后变成水潭,村里人便将它叫作“店仔口潭”。
或许是一向喜欢水的灵性,我离开老家后,每每靠近水域都会忍不住多瞧几眼。渐渐地,我发现闽南的不少水域,也藏着不尽相同的鱼类。比如笋江公园内的小湖里可以钓到螃蟹,用鱼钩挂上一小块猪肉,放入水中,当鱼竿有动静时,轻轻提起鱼线,往往就能看到一两只螃蟹挂在那块猪肉上。不同于临漳门下的河沟里有不少“土刹”,杏埔大桥至顺济新桥的那片水域,时而有江鳗出没。到了观音亭水库里,能偶遇十来斤重的草鱼,在仙人井水库的水池内,有时会看到“非洲鲫”游来游去。若是去杏埔沿江的堤岸垂钓,还可能钓到黄颡鱼。
如今,老家那些水域的模样还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从儿时的嬉戏玩耍,到后来发现闽南各处水域的独特,每一处都让我印象深刻。那些与池塘、河流等水域有关的回忆,后来慢慢变成我对家乡最深切的牵挂,也渐渐承载了我对往昔岁月最真挚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