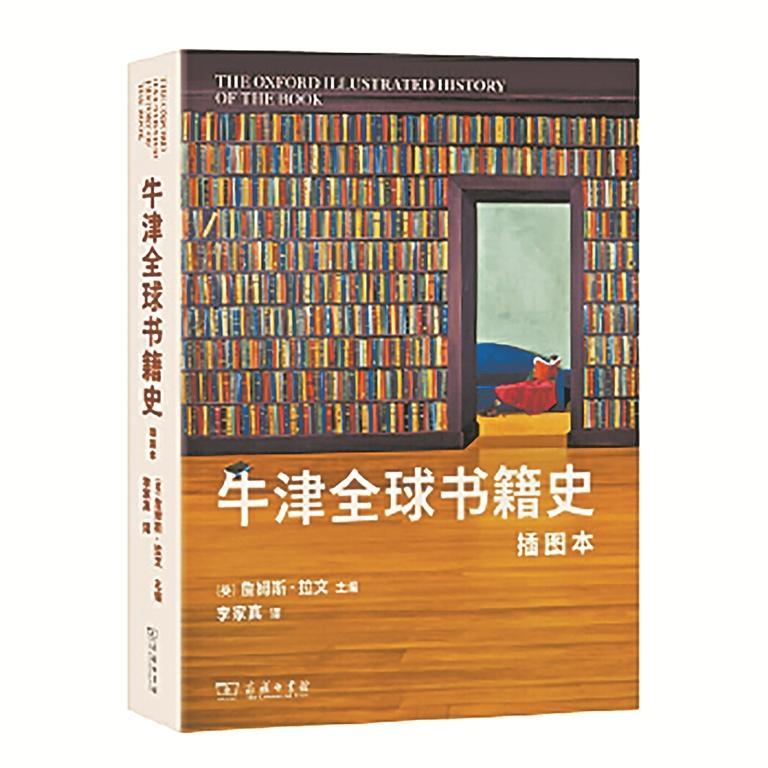一本研究书籍历史的译著,定价148元,篇幅厚达483页,似乎也没做什么宣传,却被爱书人争相购读和谈论,一传十,十传百,居然口口相传到我的耳里,让我欲罢不能。这就是插图本《牛津全球书籍史》。
近些年来,由于数字媒介的发展,我们对于书籍的传统认知已经有所动摇,次第问世的便携式电脑、智能手机和滚屏文本,样样都在挑战我们关于书籍构成、功用和目的的固有观念。在这个数字阅读日益盛行的时代,《牛津全球书籍史》的出版貌似不合时宜,事实上却是恰逢其时,逆势而上。
这部皇皇巨著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将书籍这一承载人类文明的载体置于全球史的脉络中,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全景式考察,从刻有楔形文字的黏土书版,一直讲到承载数码图文的电子书版。它告诉我们,书籍史错综复杂,至少可以上溯到5000年之前,不仅仅是纸质本册的历史,更不仅仅是印刷图书的历史,而是各个时代、各个地域的各个民族,如何出于各自不同的理由,采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努力储存、传播并取回知识和信息的历史。为本书撰文的16位作者都是各自领域的学术权威,为读者提供了众多新鲜的视角,有助于读者借由对比加深认识,了解书籍在彼此大相径庭的各个社会中曾有和现有的意义。本书正文之前的“书籍史时间线”,则可使读者直观地了解,世界各地的书籍生产和阅读历史当中,存在怎样一些出人意表的巧合和反差。如此,书籍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载体,而成为一面映照人类精神历程的明镜,一部记录文明演进的史诗。
这部著作最令人震撼之处,在于它突破了传统书籍史研究的窠臼。编者不再将目光局限于欧洲一隅,而是以全球化的视野,将中国、韩国、日本、印度、伊斯兰世界等非西方文明的书籍传统纳入研究范畴。书中明确指出,中国用印刷方法生产文本的历史比西方诸国长得多,中国的雕版印刷术推动了朝鲜和日本的早期印刷,并且在中国本土催生了三种类型的出版,即政府出版、非政府非商业出版和商业出版。从18世纪初年至19世纪中叶,中国有上亿人的识字人口在消费本国生产的印刷品,阅读群体的规模超过现代早期欧洲、日本和朝鲜阅读人口的总和。这种去中心化的叙事方式,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让读者得以在更广阔的时空维度中理解书籍与文明的互动关系。
在书籍的物质形态演变中,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的进化轨迹。从泥板到竹简,从羊皮卷到纸张,从手抄本到印刷本,每一次载体革命都伴随着文明的跃迁。书籍不仅是知识的容器,更是权力、信仰、文化的物质载体。通过考察书籍的生产、流通与阅读,我们得以窥见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碰撞,理解知识如何在时空中流转、变异与重生。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本书对书籍与权力关系的剖析。在历史的长河中,书籍既是解放思想的利器,也是规训思想的工具。从宗教典籍到世俗读物,从官方正史到民间野史,书籍始终处于权力网络的中心。通过考察书籍审查制度、出版许可制度等历史现象,本书揭示了知识生产与权力运作之间的复杂关系。
书籍存在于书本之前,换句话说,世上早就有许多传播书面文字的物品和方式。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数字技术正在重塑书籍的形态与阅读方式。但无论载体如何变迁,书籍作为人类精神载体的本质不会改变。《牛津全球书籍史》提醒我们,在拥抱技术变革的同时,更要珍视书籍所承载的人文价值。这部著作不仅是一部关于书籍的历史,更是一部关于人类如何通过书籍建构意义、传递思想、创造文明的历史。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重访书籍的历史,不仅是对过去的追忆,更是对未来的思考。当我们翻开这部厚重的书籍史,触摸到的不仅是纸张的质感,更是人类文明跳动的脉搏。在这个意义上,《牛津全球书籍史》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一曲献给人类智慧的赞歌,一部关于书籍与文明的启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