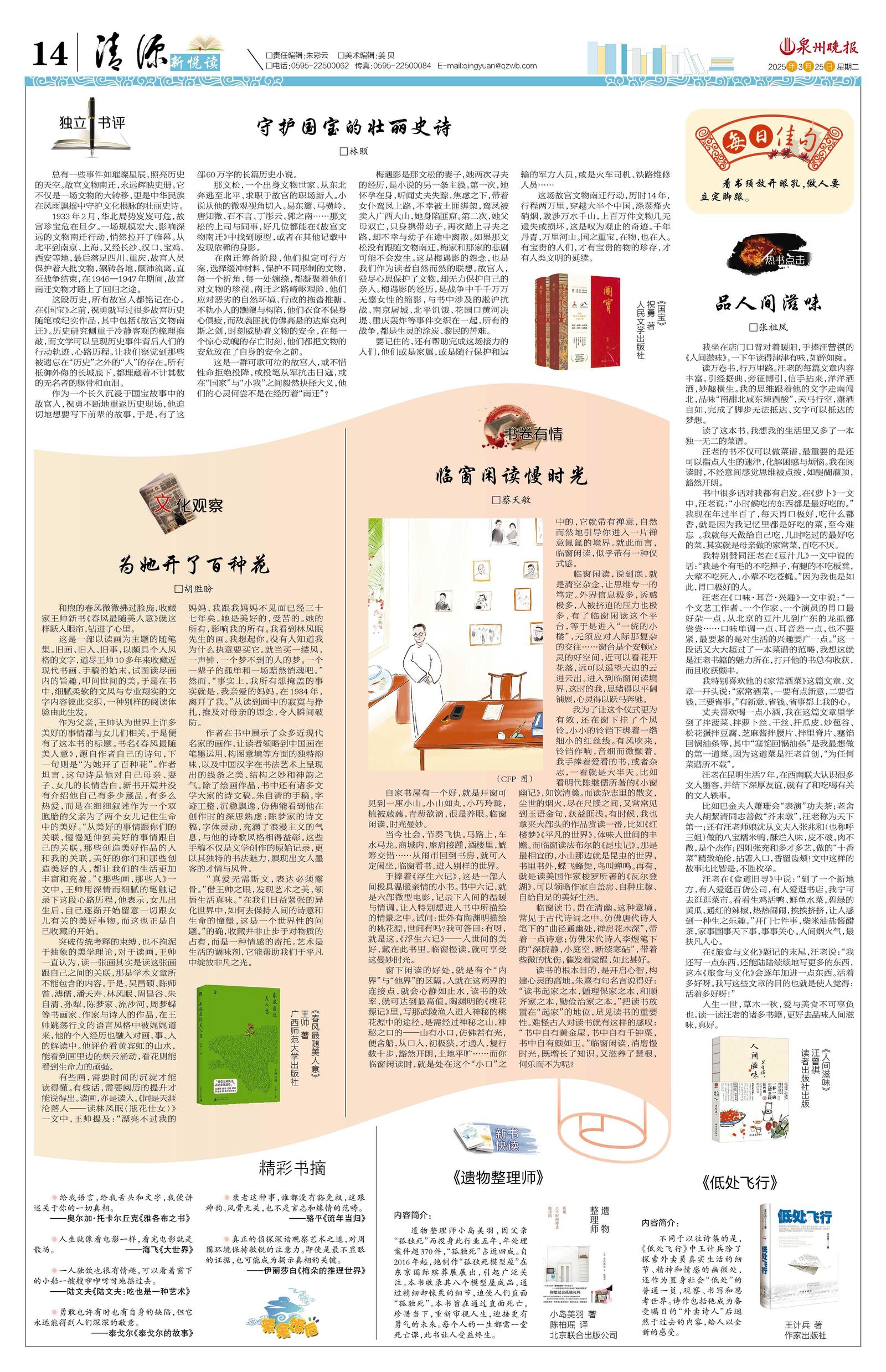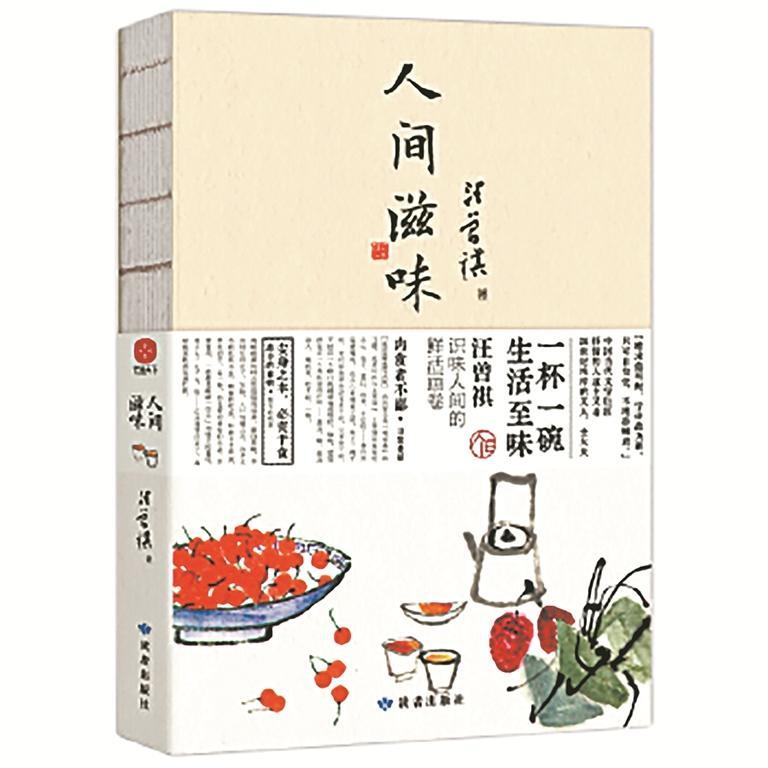我坐在店门口背对着暖阳,手捧汪曾祺的《人间滋味》,一下午读得津津有味,如醉如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汪老的每篇文章内容丰富,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洋洋洒洒,妙趣横生。我的思维跟着他的文字走南闯北,品味“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天马行空,潇洒自如,完成了脚步无法抵达、文字可以抵达的梦想。
读了这本书,我想我的生活里又多了一本独一无二的菜谱。
汪老的书不仅可以做菜谱,最重要的是还可以指点人生的迷津,化解困惑与烦恼。我在阅读时,不经意间感觉思维被点拨,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书中很多话对我都有启发。在《萝卜》一文中,汪老说:“小时候吃的东西都是最好吃的。”我现在年过半百了,每天胃口极好,吃什么都香,就是因为我记忆里都是好吃的菜,至今难忘 。我就每天做给自己吃,儿时吃过的最好吃的菜,其实就是母亲做的家常菜,百吃不厌。
我特别赞同汪老在《豆汁儿》一文中说的话:“我是个有毛的不吃掸子,有腿的不吃板凳,大荤不吃死人,小荤不吃苍蝇。”因为我也是如此,胃口极好的人。
汪老在《口味·耳音·兴趣》一文中说:“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作家、一个演员的胃口最好杂一点,从北京的豆汁儿到广东的龙虱都尝尝……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这一段话又大大超过了一本菜谱的范畴,我想这就是汪老书籍的魅力所在,打开他的书总有收获,而且收获颇丰。
我特别喜欢他的《家常酒菜》这篇文章,文章一开头说:“家常酒菜,一要有点新意,二要省钱,三要省事。”有新意,省钱、省事都上我的心。
丈夫喜欢喝一点小酒,我在这篇文章里学到了拌菠菜、拌萝卜丝、干丝、扦瓜皮、炒苞谷、松花蛋拌豆腐、芝麻酱拌腰片、拌里脊片、塞馅回锅油条等,其中“塞馅回锅油条”是我最想做的第一道菜。因为这道菜是汪老首创,“为任何菜谱所不载”。
汪老在昆明生活7年,在西南联大认识很多文人墨客,并结下深厚友谊,就有了和吃喝有关的文人轶事。
比如巴金夫人萧珊会“表演”功夫茶;老舍夫人胡絜清同志善做“芥末墩”,汪老称为天下第一;还有汪老师娘沈从文夫人张兆和(也称呼三姐)做的八宝糯米鸭,酥烂入味,皮不破,肉不散,是个杰作;四姐张充和多才多艺,做的“十香菜”精致绝伦,拈箸入口,香留齿颊!文中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汪老在《食道旧寻》中说:“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人间烟火气,最扶凡人心。
在《旅食与文化》题记的末尾,汪老说:“我还写一点东西,还能陆陆续续地写更多的东西,这本《旅食与文化》会逐年加进一点东西。活着多好呀。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呀!”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也。读一读汪老的诸多书籍,更好去品味人间滋味,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