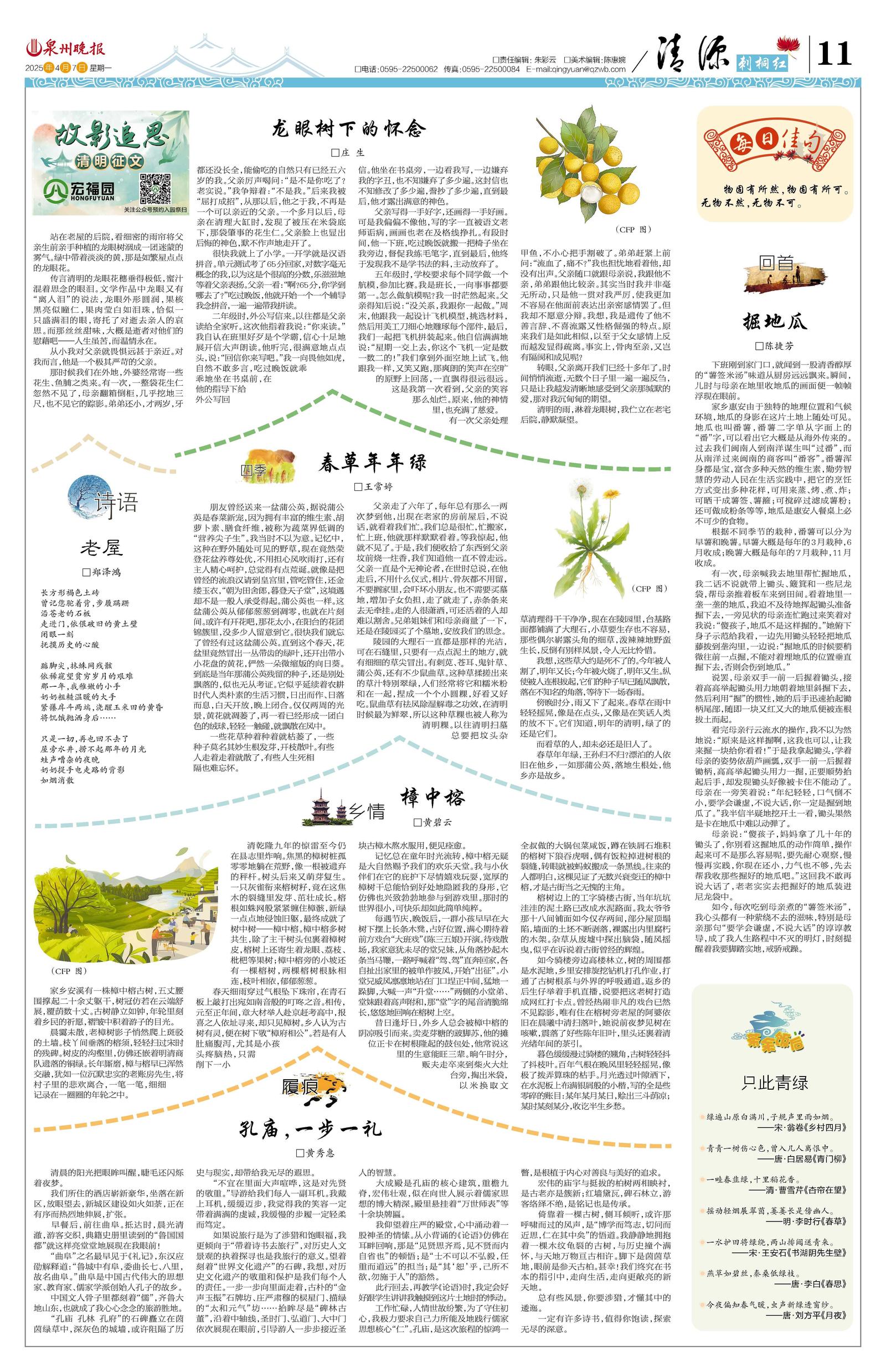站在老屋的后院,看细密的雨帘将父亲生前亲手种植的龙眼树洇成一团迷蒙的雾气。绿中带着淡淡的黄,那是如繁星点点的龙眼花。
传言清明的龙眼花穗垂得极低,蜜汁混着思念的眼泪。文学作品中龙眼又有“离人泪”的说法,龙眼外形圆润,果核黑亮似瞳仁,果肉莹白如泪珠,恰似一只盛满泪的眼,寄托了对逝去亲人的哀思。而那丝丝甜味,大概是逝者对他们的慰藉吧——人生虽苦,而温情永在。
从小我对父亲就畏惧远甚于亲近。对我而言,他是一个极其严苛的父亲。
那时候我们在外地,外婆经常寄一些花生、鱼脯之类来。有一次,一整袋花生仁忽然不见了,母亲翻箱倒柜,几乎挖地三尺,也不见它的踪影。弟弟还小,才两岁,牙都还没长全,能偷吃的自然只有已经五六岁的我。父亲厉声喝问:“是不是你吃了?老实说。”我争辩着:“不是我。”后来我被“屈打成招”,从那以后,他之于我,不再是一个可以亲近的父亲。一个多月以后,母亲在清理大缸时,发现了被压在米袋底下,那袋肇事的花生仁。父亲脸上也显出后悔的神色,默不作声地走开了。
很快我就上了小学。一开学就是汉语拼音。单元测试考了65分回家,对数字毫无概念的我,以为这是个很高的分数,乐滋滋地等着父亲表扬。父亲一看:“啊?65分,你学到哪去了?”吃过晚饭,他就开始一个一个辅导我念拼音,一遍一遍带我拼读。
二年级时,外公写信来。以往都是父亲读给全家听。这次他指着我说:“你来读。”我自认在班里好歹是个学霸,信心十足地展开信大声朗读。他听完,很满意地点点头,说:“回信你来写吧。”我一向畏他如虎,自然不敢多言,吃过晚饭就乖乖地坐在书桌前,在他的指导下给外公写回信。他坐在书桌旁,一边看我写,一边嫌弃我的字丑,也不知嫌弃了多少遍。这封信也不知修改了多少遍,誊抄了多少遍,直到最后,他才露出满意的神色。
父亲写得一手好字,还画得一手好画。可是我偏偏不像他,写的字一直被语文老师诟病,画画也老在及格线挣扎。有段时间,他一下班,吃过晚饭就搬一把椅子坐在我旁边,督促我练毛笔字,直到最后,他终于发现我不是学书法的料,主动放弃了。
五年级时,学校要求每个同学做一个航模,参加比赛。我是班长,一向事事都要第一。怎么做航模呢?我一时茫然起来。父亲得知后说:“没关系,我跟你一起做。”周末,他跟我一起设计飞机模型,挑选材料,然后用美工刀细心地雕琢每个部件,最后,我们一起把飞机拼装起来。他自信满满地说:“星期一交上去,你这个飞机一定是数一数二的!”我们拿到外面空地上试飞。他跟我一样,又笑又跑,那爽朗的笑声在空旷的原野上回荡,一直飘得很远很远。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的笑容那么灿烂。原来,他的神情里,也充满了慈爱。
有一次父亲处理甲鱼,不小心把手割破了。弟弟赶紧上前问:“流血了,痛不?”我也担忧地看着他,却没有出声。父亲随口就跟母亲说,我跟他不亲,弟弟跟他比较亲。其实当时我并非毫无所动,只是他一贯对我严厉,使我更加不容易在他面前表达出亲密感情罢了。但我却不愿意分辩。我想,我是遗传了他不善言辞、不喜流露又性格倔强的特点。原来我们是如此相似,以至于父女感情上反而越发显得疏离。事实上,骨肉至亲,又岂有隔阂和成见呢?
转眼,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时间悄悄流逝,无数个日子里一遍一遍反刍,只是让我越发清晰地感受到父亲那缄默的爱,那对我沉甸甸的期望。
清明的雨,淋着龙眼树,我伫立在老宅后院,静默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