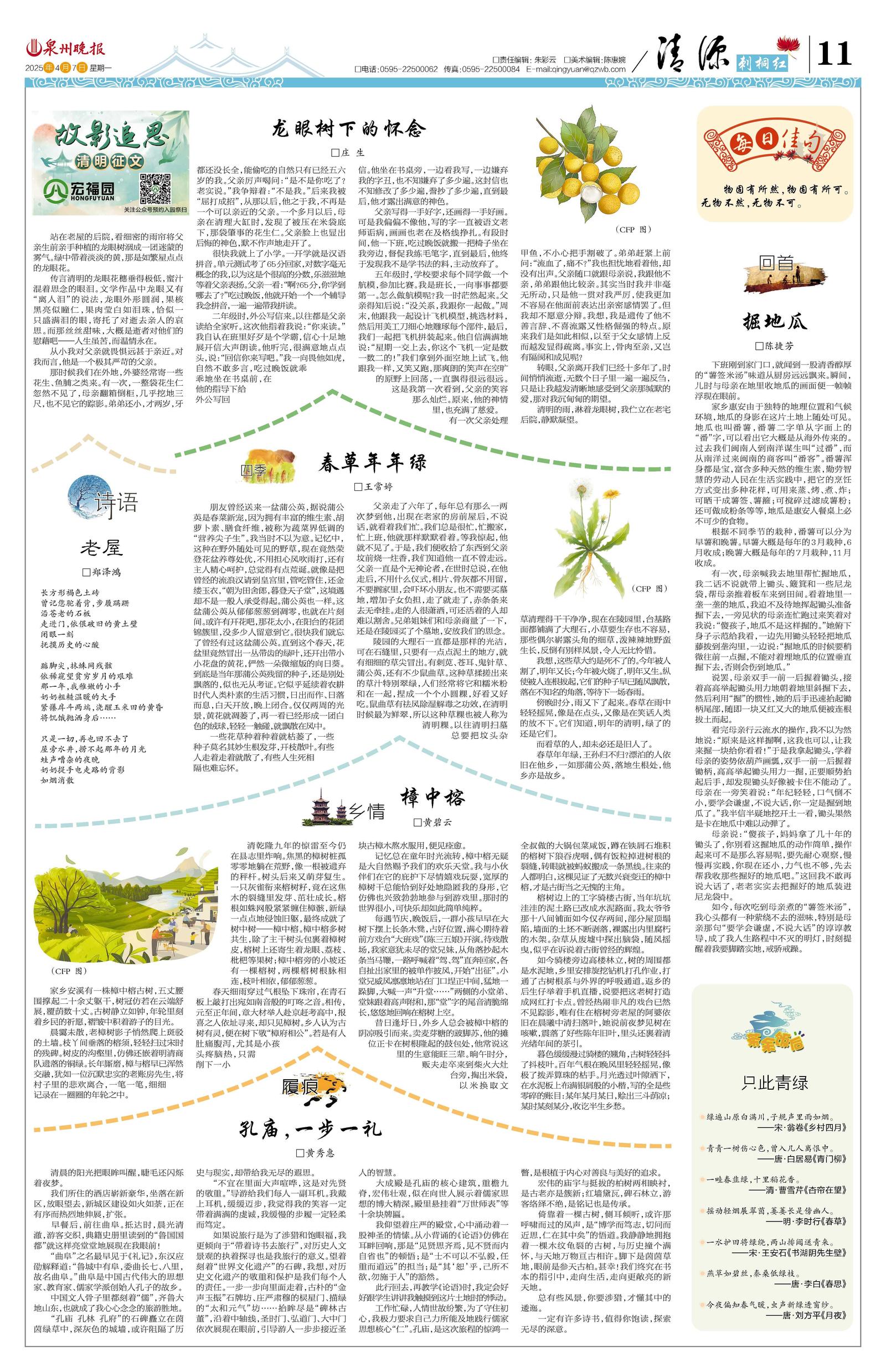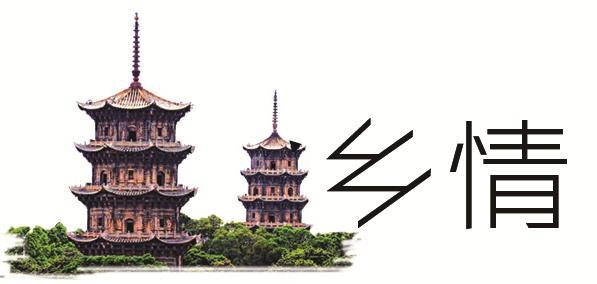家乡安溪有一株樟中榕古树,五丈腰围撑起二十余丈躯干,树冠仿若在云端舒展,覆荫数十丈。古树静立如钟,年轮里刻着乡民的祈愿,褶皱中积着游子的目光。
晨霭未散,老樟树影子悄然爬上斑驳的土墙。枝丫间垂落的榕须,轻轻扫过宋时的残碑。树皮的沟壑里,仿佛还嵌着明清商队遗落的铜绿。长年厮磨,樟与榕早已浑然交融,犹如一位沉默忠实的老账房先生,将村子里的悲欢离合,一笔一笔,细细记录在一圈圈的年轮之中。
清乾隆九年的惊雷至今仍在县志里炸响。焦黑的樟树桩孤零零地躺在荒野,像一根被遗弃的秤杆。树头后来又萌芽复生。一只灰雀衔来榕树籽,竟在这焦木的裂缝里发芽、茁壮成长。榕根如蛛网般紧紧缠住樟骸,新绿一点点地侵蚀旧躯,最终成就了树中树——樟中榕。樟中榕多树共生,除了主干树头包裹着樟树皮,榕树上还寄生着龙眼、荔枝、枇杷等果树;樟中榕旁的小坡还有一棵榕树,两棵榕树根脉相连,枝叶相依,郁郁葱葱。
春天细雨穿过气根坠下珠帘,在青石板上敲打出宛如南音般的叮咚之音。相传,元至正年间,章大材举人赴京赶考高中,报喜之人依址寻来,却只见樟树。乡人认为古树有灵,便在树下敬“樟府相公”。若是有人肚痛腹泻,尤其是小孩头疼脑热,只需削下一小块古樟木熬水服用,便见痊愈。
记忆总在童年时光流转,樟中榕无疑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欢乐天堂。我与小伙伴们在它的庇护下尽情嬉戏玩耍,宽厚的樟树干总能恰到好处地隐匿我的身形,它仿佛也兴致勃勃地参与到游戏里。那时的世界很小,可快乐却如此简单纯粹。
每遇节庆,晚饭后,一群小孩早早在大树下摆上长条木凳,占好位置,满心期待着前方戏台“大班戏”《陈三五娘》开演。待戏散场,我家意犹未尽的堂兄妹,从角落抄起木条当马鞭,一路呼喊着“驾、驾”直奔回家,各自扯出家里的被单作披风,开始“出征”。小堂兄威风凛凛地站在门口埕正中间,猛地一跺脚,大喊一声“升堂……”两侧的小堂弟、堂妹跟着高声附和,那“堂”字的尾音清脆绵长,悠悠地回响在榕树上空。
昔日逢圩日,外乡人总会被樟中榕的阴凉吸引而来。卖麦芽糖的跛脚苏,他的摊位正卡在树根隆起的鼓包处,他常说这里的生意能旺三辈。晌午时分,贩夫走卒来到柴火大灶台旁,掏出米袋,以米换取文全叔做的大锅包菜咸饭,蹲在铁屑石堆积的榕树下狼吞虎咽,偶有饭粒掉进树根的裂缝,转眼就被蚂蚁搬成一条黑线。往来的人都明白,这棵见证了无数兴衰变迁的樟中榕,才是古街当之无愧的主角。
榕树边上的工字骑楼古街,当年坑坑洼洼的泥土路已改成水泥路面。我太爷爷那十八间铺面如今仅存两间,部分屋顶塌陷,墙面的土坯不断剥落,裸露出内里腐朽的木架。杂草从废墟中探出脑袋,随风摇曳,似乎在诉说着古街曾经的辉煌。
如今骑楼旁边高楼林立,树的周围都是水泥地,乡里安排旋挖钻机打孔作业,打通了古树根系与外界的呼吸通道。返乡的后生仔举着手机直播,说要把这老树打造成网红打卡点。曾经热闹非凡的戏台已然不见踪影,唯有住在榕树旁老屋的阿婆依旧在晨曦中清扫落叶,她说前夜梦见树在咳嗽,震落了好些陈年旧叶,里头还裹着清光绪年间的茶引。
暮色缓缓漫过骑楼的翘角,古树轻轻抖了抖枝叶。百年气根在晚风里轻轻摇晃,像极了拨弄算珠的枯手。月光透过叶隙洒下,在水泥板上布满银屑般的小楷,写的全是些零碎的账目:某年某月某日,赊出三斗荫凉;某时某刻某分,收讫半生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