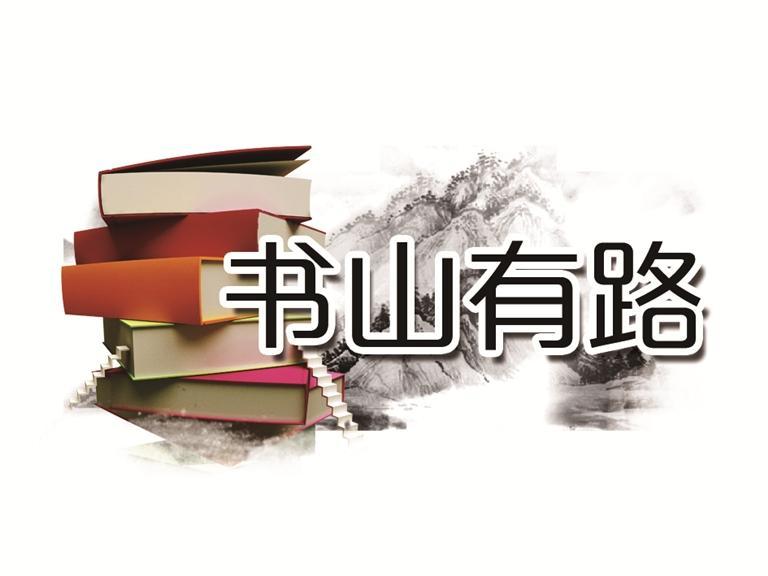我曾经历过“无书可读”的苦,后来,因偶遇泉州湾宋代古船发现者庄教授,他的一句话点拨,让我从此与历史文化结下不解之缘。
记得1974年夏日的一天,我恰巧听到农场大喇叭广播泉州湾后渚港发现古船的新闻,于是好奇地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赶到后渚港,见证发掘一艘震惊世界的宋代沉船。
当时,庄教授恰在现场考古。他见我破帽遮颜,却一直饶有兴趣、神情专注地蹲着观察了一上午,便弯下腰拍着我的肩膀问:“你喜欢考古?在哪读书?”我回答:“喜欢考古,但上山下乡,无书可读了。”教授鼓励我:“不要荒废,坚持自学,今后如有机会,可以报考大学历史系。”他的话,仿佛点亮了我心中的明灯。此后,我白天在集体农场下田劳动“挣工分忙生计”,晚上则在煤油灯下读书,憧憬着上大学。
我喜欢读书,就到各地借书来读。当时记忆力好,很多借来的书一读就记住了,有时借来的书还得连夜读,毕竟“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当时的读书条件差,借来的书读完就还给人家了,我几乎没有自己的藏书。
“机遇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机会终于来了。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由于读书打下的根基,我和弟弟从农田里拔出泥腿去赴考,双双上了分数线,虽然未被录取,但我们不灰心,再次参加了1978年夏季的高考,结果兄弟同榜,都考上大学。弟弟读中文系,我读历史系。回想起来,恢复高考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深知上大学读书来之不易,我特别珍惜,正因如此,才有后来的“书与远方”,才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40年专注陈嘉庚与南侨机工的研究之旅。
我的书房虽杂乱无章,却像一个装满宝藏的密室,书籍资料五花八门,一袋一包林林总总,很不规整。条件所限,最初,书房只是一个小角落,由一张旧桌子和简易的书架拼凑而成。那时候,我怀着对历史的懵懂好奇,开始了探索。一些老照片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通往无尽研究和深远思考的大门。
书房中,最丰富的宝藏莫过于那些讲述陈嘉庚与南侨机工的书籍。我记得第一次捧起陈嘉庚的《南侨回忆录》,那一页页微微泛黄的纸张,仿佛带着我穿越到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看到从泉州府同安县“尽尾”(集美)走出的少年,在南洋闯出一片新天地。那些关于南侨机工的史料报刊书籍,更是我反复研读的对象。我在与那些伟大的灵魂对话,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寻找最可靠的依据。
此外,相关历史时期的各类书籍也是我书房的主角,帮助我从更广阔的视角去理解历史人物的行为和贡献。
然而,我知道要真正深入研究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仅仅局限于书本知识是远远不够的。1985年,我从福建南侨机工调研开始,而后,在陈嘉庚之侄的鼓励与资助下,我背上行囊,踏上了行万里路的研究之旅。1987年起,我只身赴云贵川渝湘粤桂琼八省寻访一百多位南侨机工幸存者并作录音记录。
为了更全面地研究南侨机工,我也走出了国门,到过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八个国家与地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我深切地感受到华人在海外的奋斗历史和凝聚力。
这一路的行程,充满了挑战与惊喜:有时因资料收集困难而沮丧,有时又因新的发现而兴奋不已。旅途中,我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有的是历史学家,有的是民间文化保护者,大家一起交流探讨,让我的研究视野不断拓宽。
随着调研的深入,模糊的南侨机工形象逐渐清晰起来。1994年,我出版《陈嘉庚与南侨机工》;2015年,又出版《烽火赤子心:滇缅公路上的南侨机工》;2021年,再合作出版大型历史文献《南侨机工文史丛书》。
我的书房见证了我的成长,那些藏书是智慧的源泉。在未来的日子里,我还会继续在书斋里潜心研究,也会继续踏上那一条条充满未知的旅途。因为我深知,关于陈嘉庚与南侨机工的故事还有很多等待我去挖掘,他们的精神也将在不断探索与传承下熠熠生辉。
这一路,是与书为友、与历史对话、与伟大精神的同行之旅,也是我最热爱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