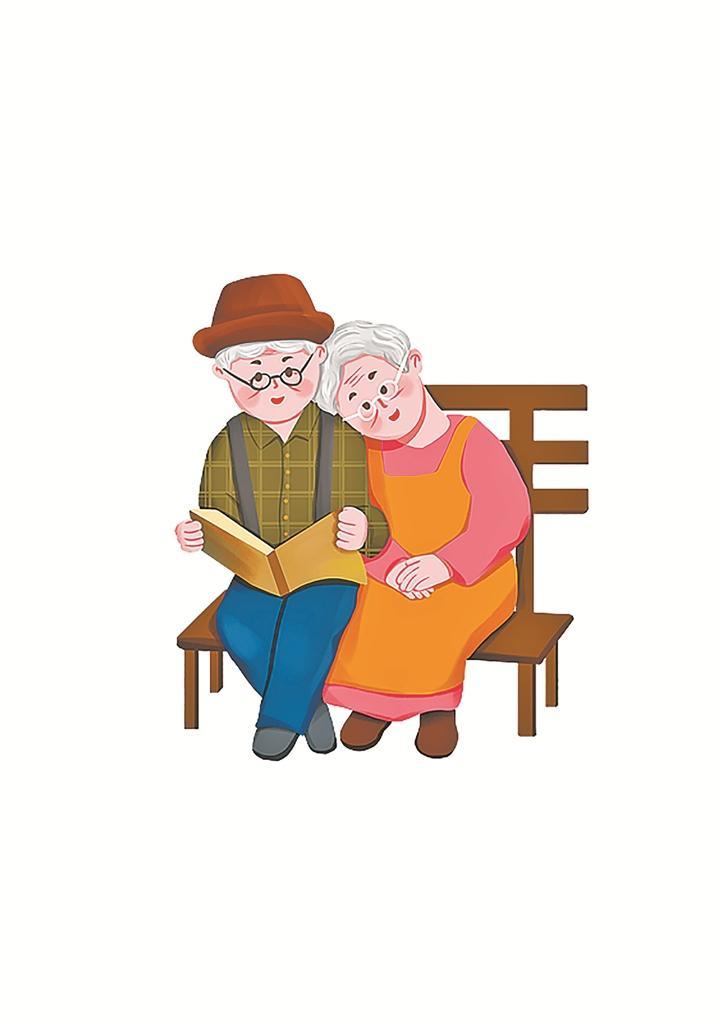父母携手走过了49个春秋,终究未能迎来金婚盛典。曾经,我们姐弟无数次憧憬着为他们举办金婚派对,甚至幻想过纪念钻石婚的盛大场景。然而,父亲离去时,母亲已被轻微脑萎缩缠上。那段日子里,她总是眼神发怔,若有所失。后来无数个日日夜夜,每当提起父亲,她只是轻声呢喃:“他……出差了。”这话像一根针,猛地扎进我们心里,既心疼母亲记忆模糊的无奈,又暗自想——若她清醒记得,又该如何承受父亲已离去的剜心之痛?
曾经的母亲,总笃定自己会走在父亲前头。她性子执拗,带着几分近乎严苛的 “洁癖”,干起活来如同不知疲倦的陀螺,非得把事情做完才肯停歇。而父亲则谨慎惜命,有时甚至显得过于小心翼翼。母亲为此常打趣他。
听家中长辈说,父母的初见是一场精心安排的相亲。彼时,父亲因家境贫寒,26岁仍未婚配。年仅19岁的母亲,听闻父亲比自己大7岁,满心以为是个沧桑的“半老头子”,说什么都不愿见面。外公外婆却一眼相中了父亲的一表人才与憨厚老实,在他们苦口婆心的劝说下,母亲才勉强点头。谁料这一见面,便是近半个世纪的相依相伴,从此命运的红线紧紧缠绕。
出嫁后,母亲第一次下厨烧火,一股脑将一大捆稻草塞进灶膛,原本熊熊燃烧的火焰瞬间被闷住,浓烟如调皮的精灵,弥漫整个厨房。等母亲手忙脚乱逃出来,早已被熏成大花脸,呛人的浓烟还引得她咳嗽不止,模样狼狈又无助。可要强的母亲怎肯认命?接下来的几天,她不顾被烟熏得通红的眼睛、呛疼的嗓子,硬是学会了烧火做饭。从那以后,她不仅将家务操持得井井有条,田间劳作也丝毫不输男丁。80多斤的瘦弱身躯,仿佛蕴藏着无尽的力量,竟能挑起一百斤的重担。父亲作为村里的文书,写得一手工整漂亮的好字,如同印刷体,可干起农活却有些笨拙。每当母亲忙完家务,父亲总会及时递上一条温热的毛巾,几十年如一日,这画面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我们姐弟的脑海中,父亲对母亲的爱藏在日复一日的细节里。
父亲对新鲜事物总是充满热忱,他毅然投身汽车配件生意,从此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那时,一封封书信成了他与家人维系情感的纽带。每次收到父亲来信,都是全家最快乐的时刻。我和姐姐总会迫不及待地抢过信件,大声朗读起来。信件开头永远是那句熟悉的“贤妻:见信好!”字里行间,满是对母亲操持家务的感激,对我们学习成长的关切。虽未直白诉说思念,可年幼的我,却能从“贤妻”二字中,感受到父亲对母亲深沉的爱。母亲回信时,总不忘让我和姐姐也写上几句。从那时起,书信在我心中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它像一首首浪漫的诗,承载着最真挚的情感。
父亲去世后的第8个年头,母亲也走了,平静地走了,应该是了无牵挂吧?在我们姐弟的记忆深处,父母从未真正离开,那些携手走过的岁月,那些柴米油盐里的温情,早已定格。他们的爱情,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却如陈年美酒,在时光的窖藏中愈发醇香,教会我们:最好的感情,是风雨同舟的坚守,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更是融入生命的相濡以沫。这份爱,也会像一颗种子,在我们心底生根发芽,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