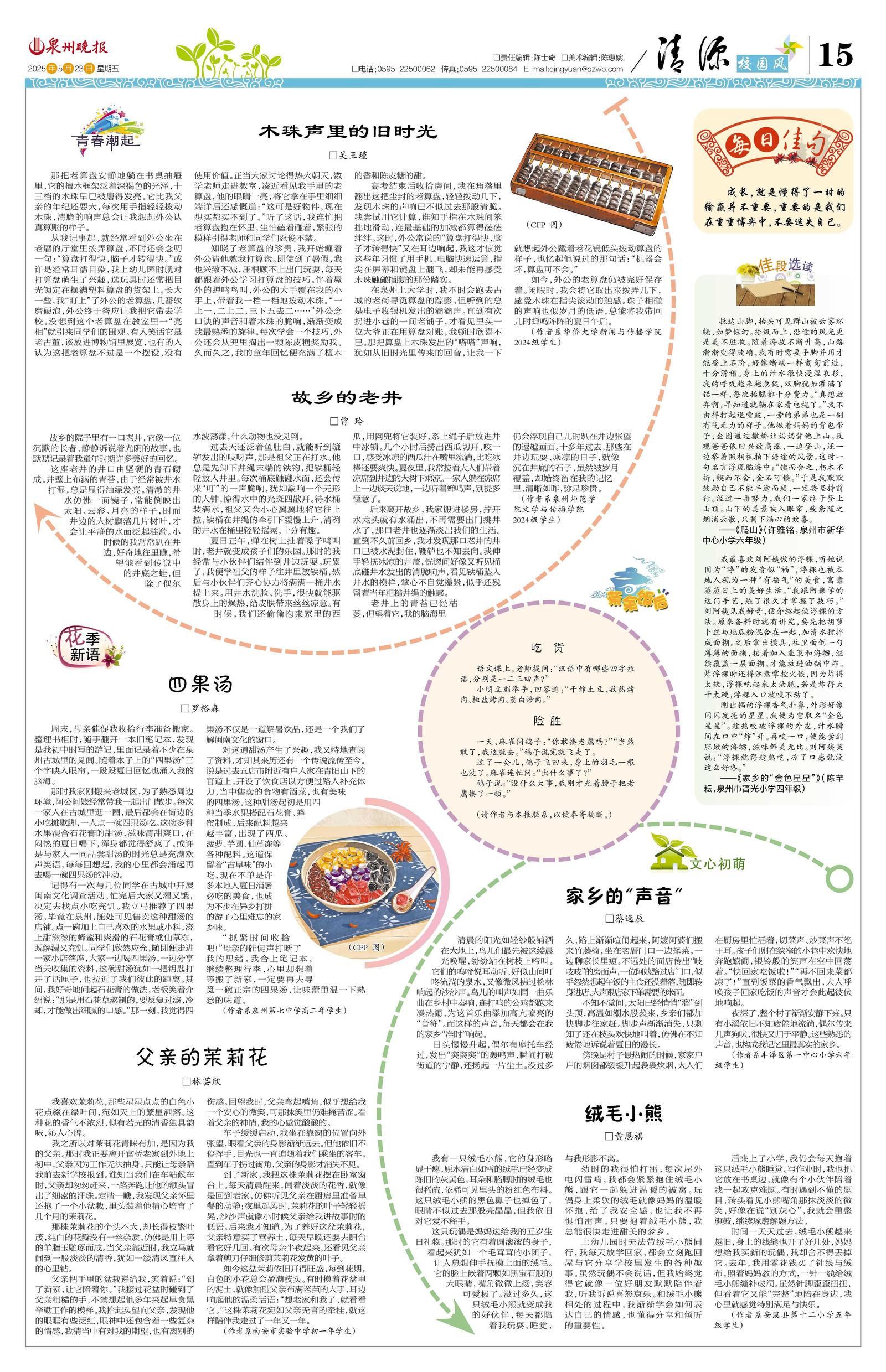那把老算盘安静地躺在书桌抽屉里,它的檀木框架泛着深褐色的光泽,十三档的木珠早已被磨得发亮。它比我父亲的年纪还要大,每次用手指轻轻拨动木珠,清脆的响声总会让我想起外公认真算账的样子。
从我记事起,就经常看到外公坐在老厝的厅堂里拨弄算盘,不时还会念叨一句:“算盘打得快,脑子才转得快。”或许是经常耳濡目染,我上幼儿园时就对打算盘萌生了兴趣,选玩具时还常把目光锁定在摆满塑料算盘的货架上。长大一些,我“盯上”了外公的老算盘,几番软磨硬泡,外公终于答应让我把它带去学校。没想到这个老算盘在教室里一“亮相”就引来同学们的围观。有人笑话它是老古董,该放进博物馆里展览,也有的人认为这把老算盘不过是一个摆设,没有使用价值。正当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数学老师走进教室,凑近看见我手里的老算盘,他的眼睛一亮,将它拿在手里细细端详后还感慨道:“这可是好物件,现在想买都买不到了。”听了这话,我连忙把老算盘抱在怀里,生怕磕着碰着,紧张的模样引得老师和同学们忍俊不禁。
知晓了老算盘的珍贵,我开始缠着外公请他教我打算盘。即使到了暑假,我也兴致不减,压根顾不上出门玩耍,每天都跟着外公学习打算盘的技巧。伴着屋外的蝉鸣鸟叫,外公的大手覆在我的小手上,带着我一档一档地拨动木珠。“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外公念口诀的声音和着木珠的脆响,渐渐变成我最熟悉的旋律。每次学会一个技巧,外公还会从兜里掏出一颗陈皮糖奖励我。久而久之,我的童年回忆便充满了檀木的香和陈皮糖的甜。
高考结束后收拾房间,我在角落里翻出这把尘封的老算盘,轻轻拨动几下,发现木珠的声响已不似过去那般清脆。我尝试用它计算,谁知手指在木珠间笨拙地滑动,连最基础的加减都算得磕磕绊绊。这时,外公常说的“算盘打得快,脑子才转得快”又在耳边响起,我这才惊觉这些年习惯了用手机、电脑快速运算,指尖在屏幕和键盘上翻飞,却未能再感受木珠触碰指腹的那份踏实。
在泉州上大学时,我不时会跑去古城的老街寻觅算盘的踪影,但听到的总是电子收银机发出的滴滴声。直到有次拐进小巷的一间老铺子,才看见里头一位大爷正在用算盘对账,我顿时欣喜不已。那把算盘上木珠发出的“嗒嗒”声响,犹如从旧时光里传来的回音,让我一下就想起外公戴着老花镜低头拨动算盘的样子,也忆起他说过的那句话:“机器会坏,算盘可不会。”
如今,外公的老算盘仍被完好保存着。闲暇时,我会将它取出来拨弄几下,感受木珠在指尖滚动的触感。珠子相碰的声响也似岁月的低语,总能将我带回儿时蝉鸣阵阵的夏日午后。
(作者系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4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