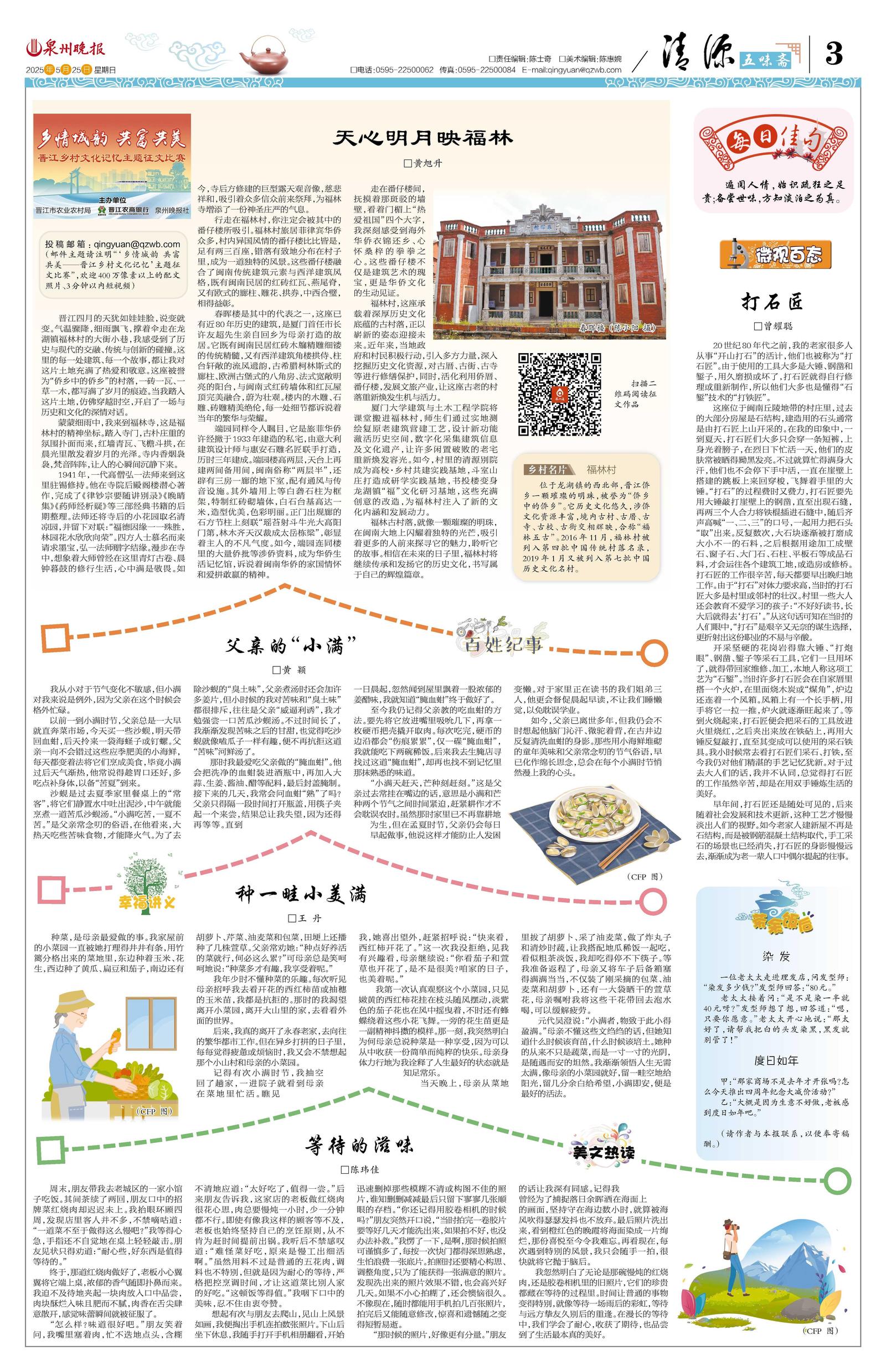我从小对于节气变化不敏感,但小满对我来说是例外,因为父亲在这个时候会格外忙碌。
以前一到小满时节,父亲总是一大早就直奔菜市场,今天买一些沙蚬,明天带回血蚶,后天拎来一袋海蛏子或钉螺。父亲一向不会错过这些应季肥美的小海鲜,每天都变着法将它们烹成美食,毕竟小满过后天气渐热,他常说得趁胃口还好,多吃点补身体,以备“苦夏”到来。
沙蚬是过去夏季家里餐桌上的“常客”,将它们静置水中吐出泥沙,中午就能烹煮一道苦瓜沙蚬汤。“小满吃苦,一夏不苦。”是父亲常念叨的俗语,在他看来,大热天吃些苦味食物,才能降火气。为了去除沙蚬的“臭土味”,父亲煮汤时还会加许多姜片,但小时候的我对苦味和“臭土味”都很排斥,往往是父亲“威逼利诱”,我才勉强尝一口苦瓜沙蚬汤。不过时间长了,我渐渐发现苦味之后的甘甜,也觉得吃沙蚬就像嗑瓜子一样有趣,便不再抗拒这道“苦味”河鲜汤了。
那时我最爱吃父亲做的“腌血蚶”。他会把洗净的血蚶装进酒瓶中,再加入大蒜、生姜、酱油、醋等配料,最后封盖腌制。接下来的几天,我常会问血蚶“熟”了吗?父亲只得隔一段时间打开瓶盖,用筷子夹起一个来尝,结果总让我失望,因为还得再等等。直到一日晨起,忽然闻到屋里飘着一股浓郁的姜醋味,我就知道“腌血蚶”终于做好了。
至今我仍记得父亲教的吃血蚶的方法。要先将它放进嘴里吸吮几下,再拿一枚硬币把壳撬开取肉。每次吃完,硬币的边沿都会“伤痕累累”,仅一碟“腌血蚶”,我就能吃下两碗稀饭。后来我去生腌店寻找过这道“腌血蚶”,却再也找不到记忆里那抹熟悉的味道。
“小满天赶天,芒种刻赶刻。”这是父亲过去常挂在嘴边的话,意思是小满和芒种两个节气之间时间紧迫,赶紧耕作才不会耽误农时。虽然那时家里已不再靠耕地为生,但在孟夏时节,父亲仍会每日早起做事,他说这样才能防止人发困变懒。对于家里正在读书的我们姐弟三人,他更会督促晨起早读,不让我们睡懒觉,以免耽误学业。
如今,父亲已离世多年,但我仍会不时想起他脑门沁汗、微驼着背,在古井边反复清洗血蚶的身影。那些用小海鲜堆砌的童年美味和父亲常念叨的节气俗语,早已化作绵长思念,总会在每个小满时节悄然漫上我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