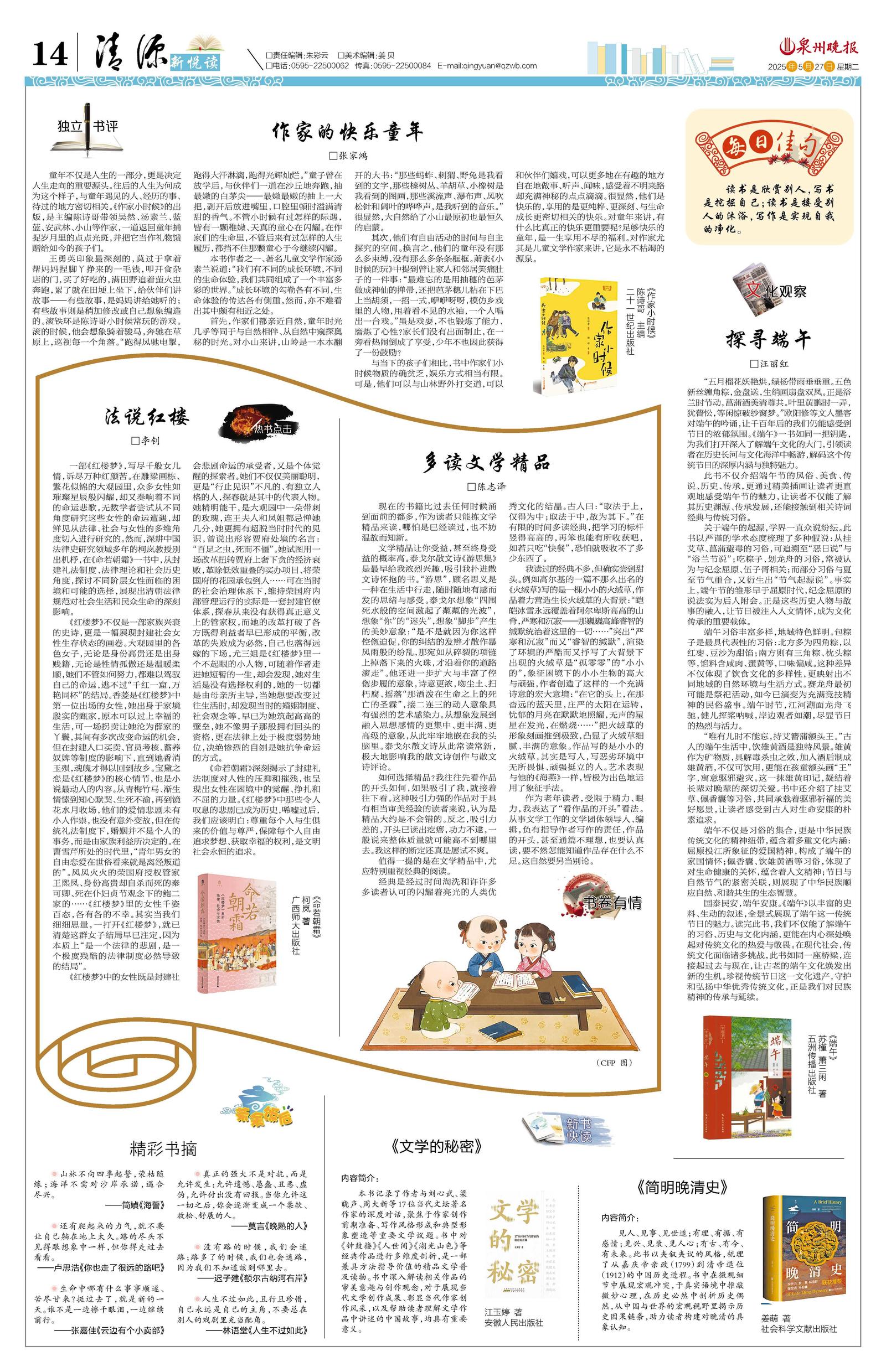□张家鸿
童年不仅是人生的一部分,更是决定人生走向的重要源头。往后的人生为何成为这个样子,与童年遇见的人、经历的事、待过的地方密切相关。《作家小时候》的出版,是主编陈诗哥带领吴然、汤素兰、蓝蓝、安武林、小山等作家,一道返回童年捕捉岁月里的点点光斑,并把它当作礼物馈赠给如今的孩子们。
王勇英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拿着帮妈妈捏脚丫挣来的一毛钱,叩开食杂店的门,买了好吃的,满田野追着萤火虫奔跑,累了就在田埂上坐下,给伙伴们讲故事——有些故事,是妈妈讲给她听的;有些故事则是稍加修改或自己想象编造的。滚铁环是陈诗哥小时候常玩的游戏。滚的时候,他会想象骑着骏马,奔驰在草原上,巡视每一个角落。“跑得风驰电掣,跑得大汗淋漓,跑得光辉灿烂。”童子曾在放学后,与伙伴们一道在沙丘地奔跑,抽最嫩的白茅尖——最嫩最嫩的抽上一大把,剥开后放进嘴里,口腔里顿时溢满清甜的香气。不管小时候有过怎样的际遇,皆有一颗稚嫩、天真的童心在闪耀。在作家们的生命里,不管后来有过怎样的人生履历,都挡不住那颗童心于今继续闪耀。
本书作者之一、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说道:“我们有不同的成长环境,不同的生命体验,我们共同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成长环境的勾勒各有不同,生命体验的传达各有侧重,然而,亦不难看出其中颇有相近之处。
首先,作家们都亲近自然,童年时光几乎等同于与自然相伴、从自然中窥探奥秘的时光。对小山来讲,山岭是一本本翻开的大书:“那些蚂蚱、刺猬、野兔是我看到的文字,那些榛树丛、羊胡草、小橡树是我看到的图画,那些溪流声、瀑布声、风吹松针和阔叶的哗哗声,是我听到的音乐。”很显然,大自然给了小山最原初也最恒久的启蒙。
其次,他们有自由活动的时间与自主探究的空间。换言之,他们的童年没有那么多束缚,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萧袤《小时候的玩》中提到曾让家人和邻居笑痛肚子的一件事:“最难忘的是用抽穗的芭茅做成神仙的掸帚,还把芭茅穗儿粘在下巴上当胡须,一招一式,咿咿呀呀,模仿乡戏里的人物,甩着看不见的水袖,一个人唱出一台戏。”虽是戏耍,不也锻炼了能力、磨炼了心性?家长们没有出面制止,在一旁看热闹倒成了享受,少年不也因此获得了一份鼓励?
与当下的孩子们相比,书中作家们小时候物质的确贫乏,娱乐方式相当有限。可是,他们可以与山林野外打交道,可以和伙伴们嬉戏,可以更多地在有趣的地方自在地做事、听声、闻味,感受着不明来路却充满神秘的点点滴滴。很显然,他们是快乐的,享用的是更纯粹、更深刻、与生命成长更密切相关的快乐。对童年来讲,有什么比真正的快乐更重要呢?足够快乐的童年,是一生享用不尽的福利。对作家尤其是儿童文学作家来讲,它是永不枯竭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