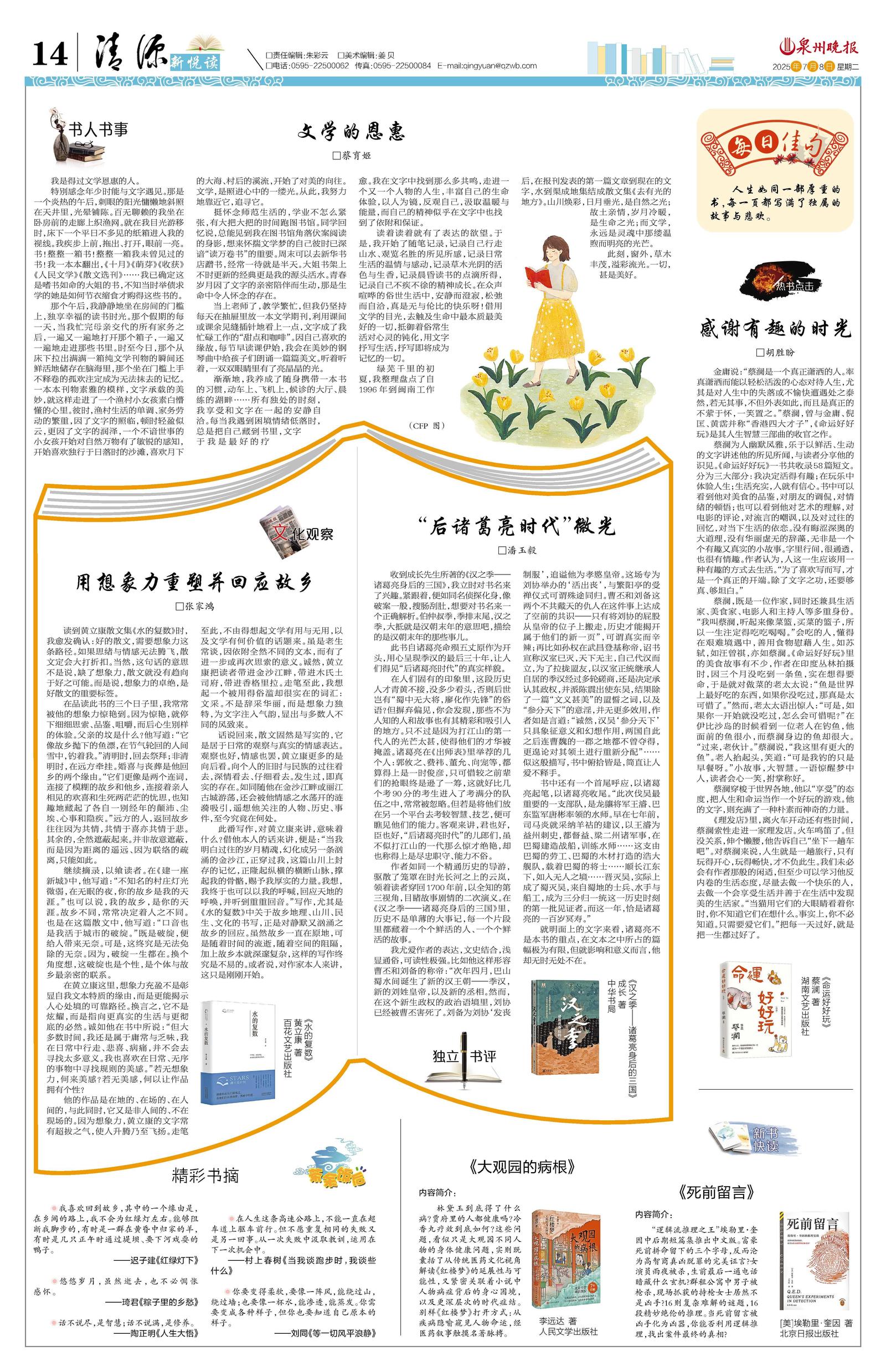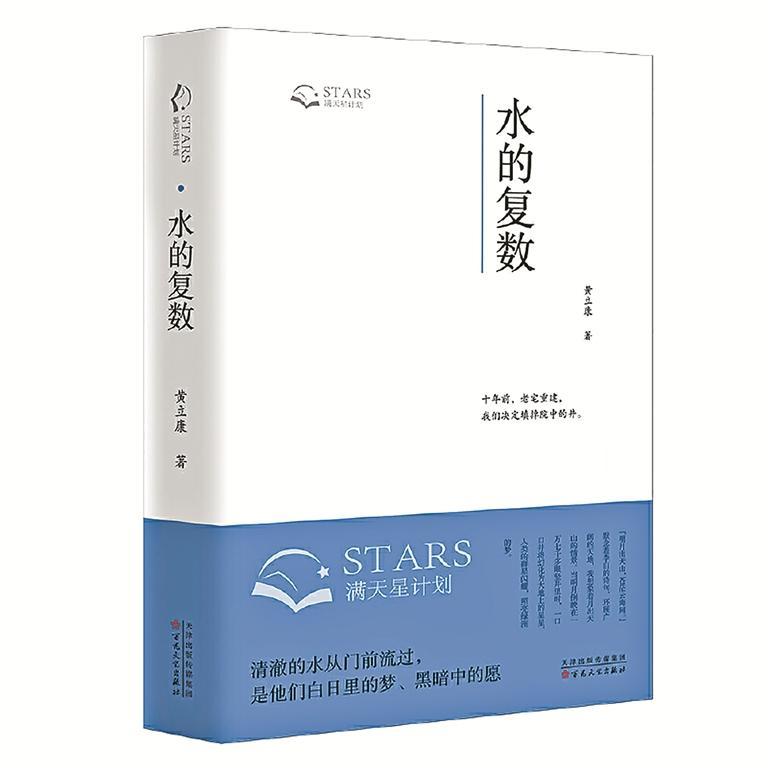□张家鸿
读到黄立康散文集《水的复数》时,我愈发确认:好的散文,需要想象力这条路径。如果思绪与情感无法腾飞,散文定会大打折扣。当然,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缺了想象力,散文就没有趋向于好之可能。而是说,想象力的卓绝,是好散文的重要标签。
在品读此书的三个日子里,我常常被他的想象力惊艳到。因为惊艳,就停下细细思索、品鉴、咀嚼,而后心生别样的体验。父亲的坟是什么?他写道:“它像故乡抛下的鱼漂,在节气轮回的人间雪中,钓着我。”清明时,回去祭拜;非清明时,在远方牵挂。婚喜与丧葬是他回乡的两个缘由。“它们更像是两个连词,连接了模糊的故乡和他乡,连接着亲人相见的欢喜和生死两茫茫的忧思,也知趣地藏起了各自一别经年的颠沛、尘埃、心事和隐疾。”远方的人,返回故乡往往因为共情,共情于喜亦共情于悲。其余的,全然遮蔽起来。并非故意遮蔽,而是因为距离的遥远、因为联络的疏离,只能如此。
继续摘录,以飨读者。在《建一座新城》中,他写道:“不知名的村庄灯光微弱,在无眠的夜,你的故乡是我的天涯。”也可以说,我的故乡,是你的天涯。故乡不同,常常决定着人之不同。也是在这篇散文中,他写道:“口音也是我活于城市的破绽。”既是破绽,便给人带来无奈。可是,这终究是无法免除的无奈。因为,破绽一生都在。换个角度想,这破绽也是个性,是个体与故乡最亲密的联系。
在黄立康这里,想象力充盈不是彰显自我文本特质的缘由,而是更能揭示人心处境的可靠路径。换言之,它不是炫耀,而是指向更真实的生活与更彻底的必然。诚如他在书中所说:“但大多数时间,我还是属于庸常与乏味,我在日常中行走、悲喜、病痛,并不会去寻找太多意义。我也喜欢在日常、无序的事物中寻找规则的美感。”若无想象力,何来美感?若无美感,何以让作品拥有个性?
他的作品是在地的、在场的、在人间的,与此同时,它又是非人间的、不在现场的。因为想象力,黄立康的文字常有超拔之气,使人升腾乃至飞扬。走笔至此,不由得想起文学有用与无用,以及文学有何价值的话题来。虽是老生常谈,因依附全然不同的文本,而有了进一步或再次思索的意义。诚然,黄立康把读者带进金沙江畔,带进木氏土司府,带进香格里拉。走笔至此,我想起一个被用得俗滥却很实在的词汇:文采。不是辞采华丽,而是想象力独特,为文字注入气韵,显出与多数人不同的风致来。
话说回来,散文固然是写实的,它是居于日常的观察与真实的情感表达。观察也好,情感也罢,黄立康更多的是向后看。向个人的旧时与民族的过往看去,深情看去、仔细看去。发生过,即真实的存在。如同随他在金沙江畔或丽江古城游荡,还会被他情感之水荡开的涟漪吸引,遥想他关注的人物、历史、事件,至今究竟在何处。
此番写作,对黄立康来讲,意味着什么?借他本人的话来讲,便是:“当我明白过往的岁月精魂,幻化成另一条汹涌的金沙江,正穿过我,这篇山川上封存的记忆,正隆起纵横的横断山脉,撑起我的骨骼,赐予我厚实的力量。我想,我终于也可以以我的呼喊,回应天地的呼唤,并听到重重回音。”写作,尤其是《水的复数》中关于故乡地理、山川、民生、文化的书写,正是对静默又汹涌之故乡的回应。虽然故乡一直在原地,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空间的阻隔,加上故乡本就深邃复杂,这样的写作终究是不易的。或者说,对作家本人来讲,这只是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