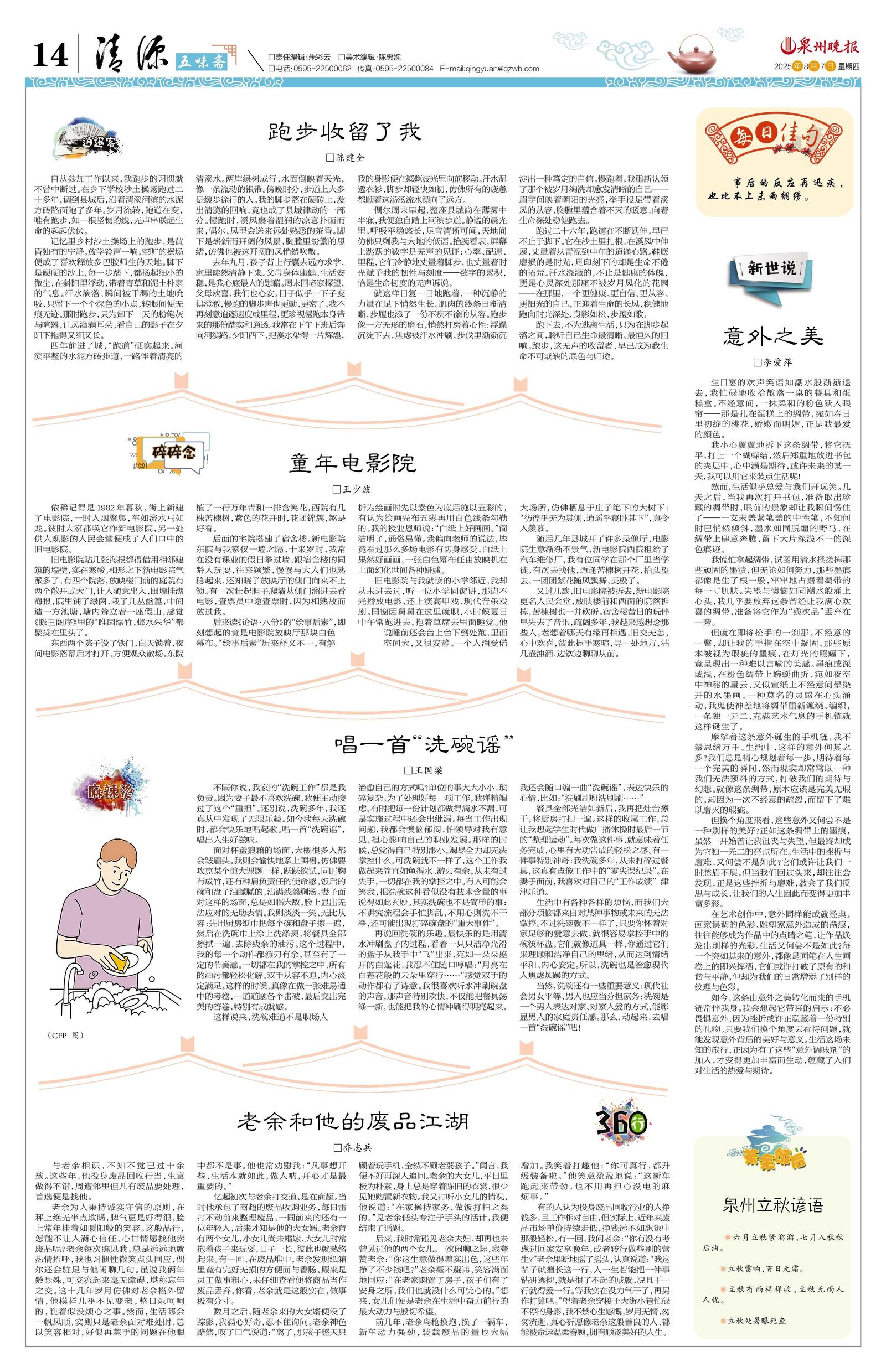依稀记得是1982年暮秋,街上新建了电影院,一时人烟聚集,车如流水马如龙。彼时大家都唤它作新电影院,另一处供人观影的人民会堂便成了人们口中的旧电影院。
旧电影院贴几张海报都得借用相邻建筑的墙壁,实在寒酸。相形之下新电影院气派多了,有四个院落,放映楼门前的庭院有两个敞开式大门,让人随意出入,围墙挂满海报,院里铺了绿茵,栽了几丛幽篁,中间造一方池塘,塘内耸立着一座假山,感觉《滕王阁序》里的“睢园绿竹,邺水朱华”都聚拢在里头了。
东西两个院子设了铁门,白天锁着,夜间电影落幕后才打开,方便观众散场。东院植了一行万年青和一排含笑花,西院有几株苦楝树,紫色的花开时,花团锦簇,煞是好看。
后面的宅院搭建了宿舍楼。新电影院东院与我家仅一墙之隔,十来岁时,我常在没有课业的假日攀过墙,跟宿舍楼的同龄人玩耍,往来频繁,慢慢与大人们也熟稔起来,还知晓了放映厅的侧门向来不上锁。有一次壮起胆子爬墙从侧门溜进去看电影,查票员中途查票时,因为相熟故而放过我。
后来读《论语·八佾》的“绘事后素”,即刻想起的竟是电影院放映厅那块白色幕布。“绘事后素”历来释义不一,有解析为绘画时先以素色为底后施以五彩的,有认为绘画先布五彩再用白色线条勾勒的。我的授业恩师说:“白纸上好画画。”简洁明了,通俗易懂。我偏向老师的说法,毕竟看过那么多场电影有切身感受,白纸上果然好画画,一张白色幕布任由放映机在上面幻化世间各种妍媸。
旧电影院与我就读的小学邻近,我却从未进去过,听一位小学同窗讲,那边不光播放电影,还上演高甲戏、现代音乐戏剧。同窗因舅舅在这里就职,小时候夏日中午常跑进去,抱着草席去里面睡觉。他说睡前还会台上台下到处跑,里面空间大,又很安静。一个人消受偌大场所,仿佛栖息于庄子笔下的大树下:“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真令人羡慕。
随后几年县城开了许多录像厅,电影院生意渐渐不景气,新电影院西院租给了汽车维修厂,我有位同学在那个厂里当学徒,有次去找他,适逢苦楝树开花,抬头望去,一团团紫花随风飘舞,美极了。
又过几载,旧电影院被拆去,新电影院更名人民会堂,放映楼前和西面的院落拆掉,苦楝树也一并砍斫。宿舍楼昔日的玩伴早失去了音讯,疏阔多年,我越来越想念那些人,老想着哪天有缘再相遇,旧交无恙,心中欢喜,彼此握手寒暄,寻一处地方,沽几壶浊酒,边饮边聊聊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