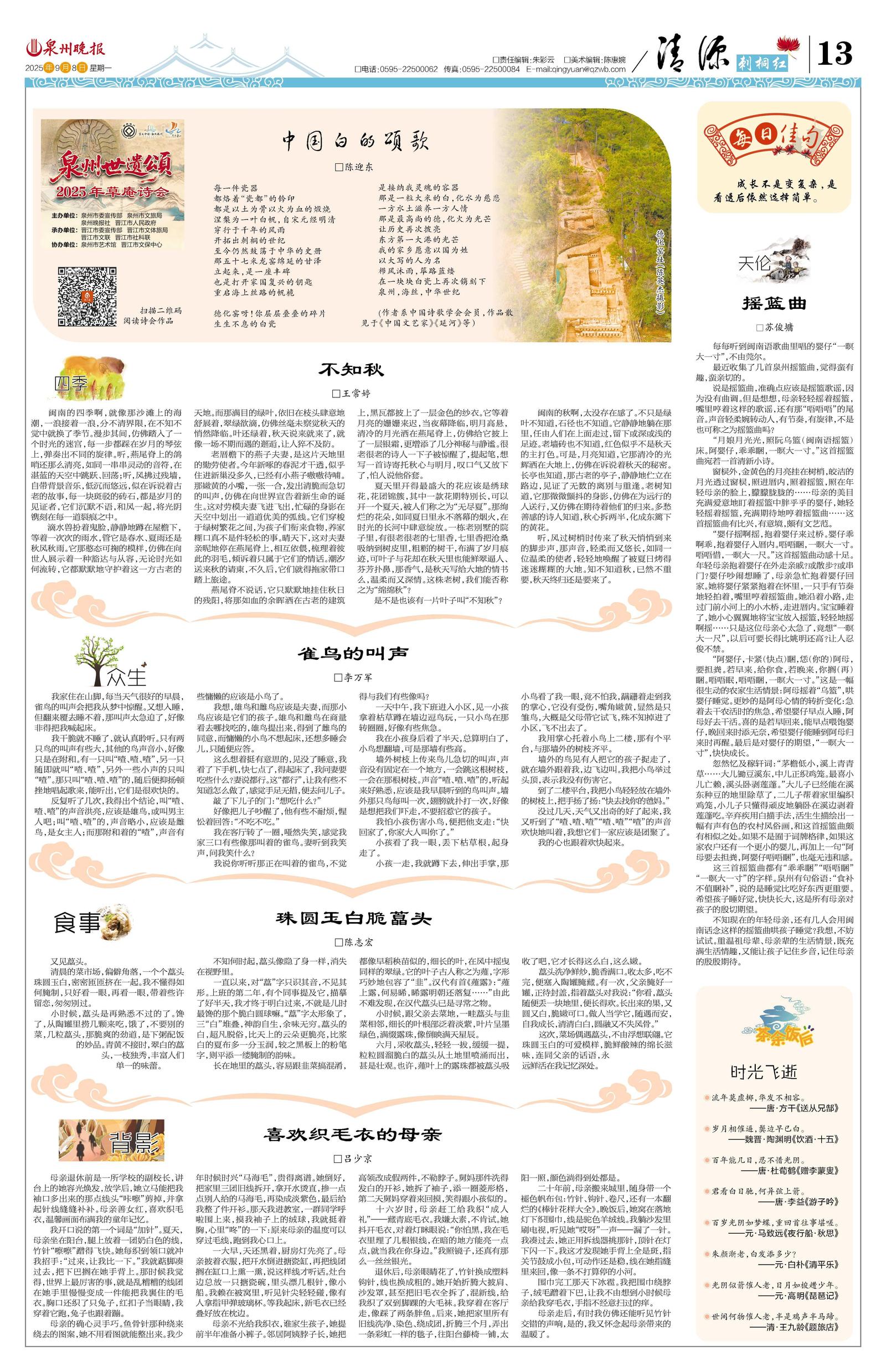母亲退休前是一所学校的副校长,讲台上的她容光焕发,放学后,她立马能把我袖口多出来的那点线头“咔嚓”剪掉,并拿起针线缝缝补补。母亲善女红,喜欢织毛衣,温馨画面布满我的童年记忆。
我开口说的第一个词是“加针”。夏天,母亲坐在阳台,腿上放着一团奶白色的线,竹针“嚓嚓”蹭得飞快。她每织到领口就冲我招手:“过来,让我比一下。”我就踮脚凑过去,把下巴搁在她手背上。那时候我觉得,世界上最厉害的事,就是乱糟糟的线团在她手里慢慢变成一件能把我裹住的毛衣。胸口还织了只兔子,红扣子当眼睛,我穿着它跑,兔子也跟着蹦。
母亲的确心灵手巧。鱼骨针那种绕来绕去的图案,她不用看图就能整出来。我少年时候时兴“马海毛”,贵得离谱。她倒好,把家里三团旧线拆开,拿开水烫直,掺一点点别人给的马海毛,再染成淡紫色,最后给我整了件开衫。那天我进教室,一群同学呼啦围上来,摸我袖子上的绒球,我就挺着胸,心里“咚”的一下:原来母亲的温度可以穿过毛线,跑到我心口上。
一大早,天还黑着,厨房灯先亮了。母亲披着衣服,把开水倒进搪瓷缸,再把线团搁在缸口上熏一熏,说这样线才听话。灶台边总放一只搪瓷碗,里头漂几根针,像小船。我赖在被窝里,听见针尖轻轻碰,像有人拿指甲弹玻璃杯。等我起床,新毛衣已经叠好放在枕边。
母亲不光给我织衣,谁家生孩子,她提前半年准备小裤子。邻居阿姨脖子长,她把高领改成假两件,不勒脖子。舅妈那件洗得发白的开衫,她拆了袖子,添一圈菱形格,第二天舅妈穿着来回摸,笑得跟小孩似的。
十六岁时,母亲赶工给我织“成人礼”——藏青底毛衣。我嫌太素,不肯试。她抖开毛衣,对着灯眯眼说:“你怕黑,我在毛衣里埋了几根银线,在暗的地方能亮一点点,就当我在你身边。”我照镜子,还真有那么一丝丝银光。
退休后,母亲眼睛花了,竹针换成塑料钩针,线也换成粗的。她开始折腾大披肩、沙发罩,甚至把旧毛衣全拆了,混新线,给我织了双到脚踝的大毛袜。我穿着在客厅走,像踩了两条胖鱼。后来,她把家里所有旧线洗净、染色、绕成团,折腾三个月,弄出一条彩虹一样的毯子,往阳台藤椅一铺,太阳一照,颜色淌得到处都是。
二十年前,母亲搬来城里,随身带一个褪色帆布包:竹针、钩针、卷尺,还有一本翻烂的《棒针花样大全》。晚饭后,她窝在落地灯下织围巾,线是驼色羊绒线。我躺沙发里刷电视,听见她“哎呀”一声——漏了一针。我凑过去,她正用拆线器挑那针,顶针在灯下闪一下。我这才发现她手背上全是斑,指关节鼓成小包,可动作还是稳,线在她指缝里来回,像一条不打算停的小河。
围巾完工那天下冰雹。我把围巾绕脖子,绒毛蹭着下巴,让我不由想到小时候母亲给我穿毛衣,手指不经意扫过的痒。
母亲走后,有时我仿佛还能听见竹针交错的声响,是的,我又怀念起母亲带来的温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