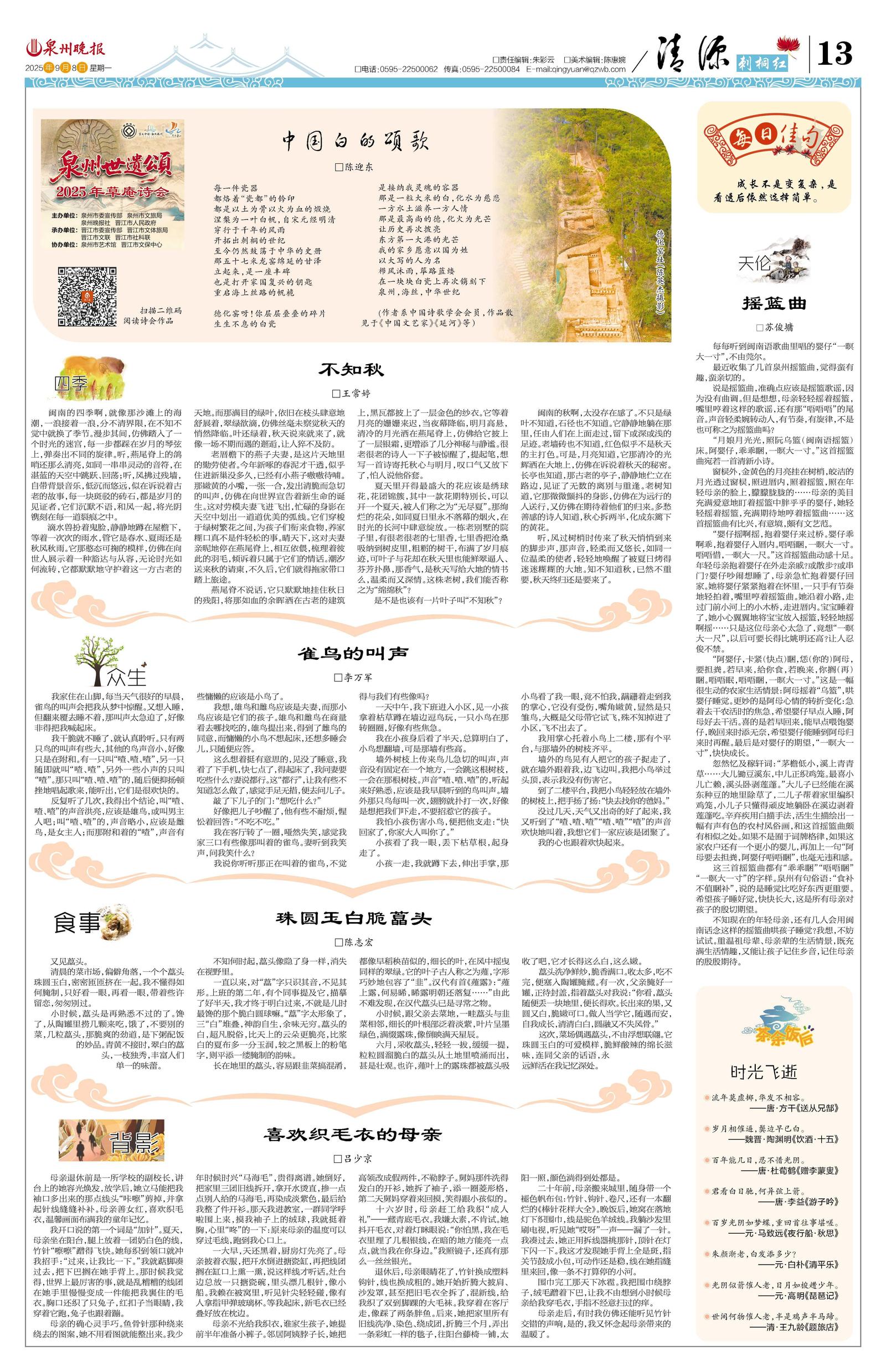又见藠头。
清晨的菜市场,偏僻角落,一个个藠头珠圆玉白,密密匝匝挤在一起。我不懂得如何腌制,只好看一眼,再看一眼,带着些许留恋,匆匆别过。
小时候,藠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馋了,从陶罐里捞几颗来吃,饿了,不要别的菜,几粒藠头,那脆爽的劲道,是下粥配饭的妙品。青黄不接时,翠白的藠头,一枝独秀,丰富人们单一的味蕾。
不知何时起,藠头像隐了身一样,消失在视野里。
一直以来,对“藠”字只识其音,不见其形。上班的第二年,有个同事提及它,描摹了好半天,我才终于明白过来,不就是儿时最馋的那个脆白圆球嘛。“藠”字太形象了,三“白”堆叠,神韵自生,余味无穷。藠头的白,超凡脱俗,比天上的云朵更脆亮,比浆白的夏布多一分玉润,较之黑板上的粉笔字,则平添一缕腌制的韵味。
长在地里的藠头,容易跟韭菜搞混淆,都像早稻秧苗似的,细长的叶,在风中摇曳同样的翠绿。它的叶子古人称之为薤,字形巧妙地包容了“韭”。汉代有首《薤露》:“薤上露,何易晞,晞露明朝还落复……”由此不难发现,在汉代藠头已是寻常之物。
小时候,跟父亲去菜地,一畦藠头与韭菜相邻,细长的叶根部泛着淡紫,叶片呈墨绿色,满缀露珠,像倒映满天星辰。
六月,采收藠头,轻轻一拔,缓缓一提,粒粒圆溜脆白的藠头从土地里喷涌而出,甚是壮观。也许,薤叶上的露珠都被藠头吸收了吧,它才长得这么白,这么嫩。
藠头洗净鲜炒,脆香满口。收太多,吃不完,便塞入陶罐腌藏。有一次,父亲腌好一罐,正待封盖,指着藠头对我说:“你看,藠头随便丢一块地里,便长得欢。长出来的果,又圆又白,脆嫩可口。做人当学它,随遇而安,自我成长,清清白白,圆融又不失风骨。”
这次,菜场偶遇藠头,不由浮想联翩。它珠圆玉白的可爱模样,脆鲜酸辣的绵长滋味,连同父亲的话语,永远鲜活在我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