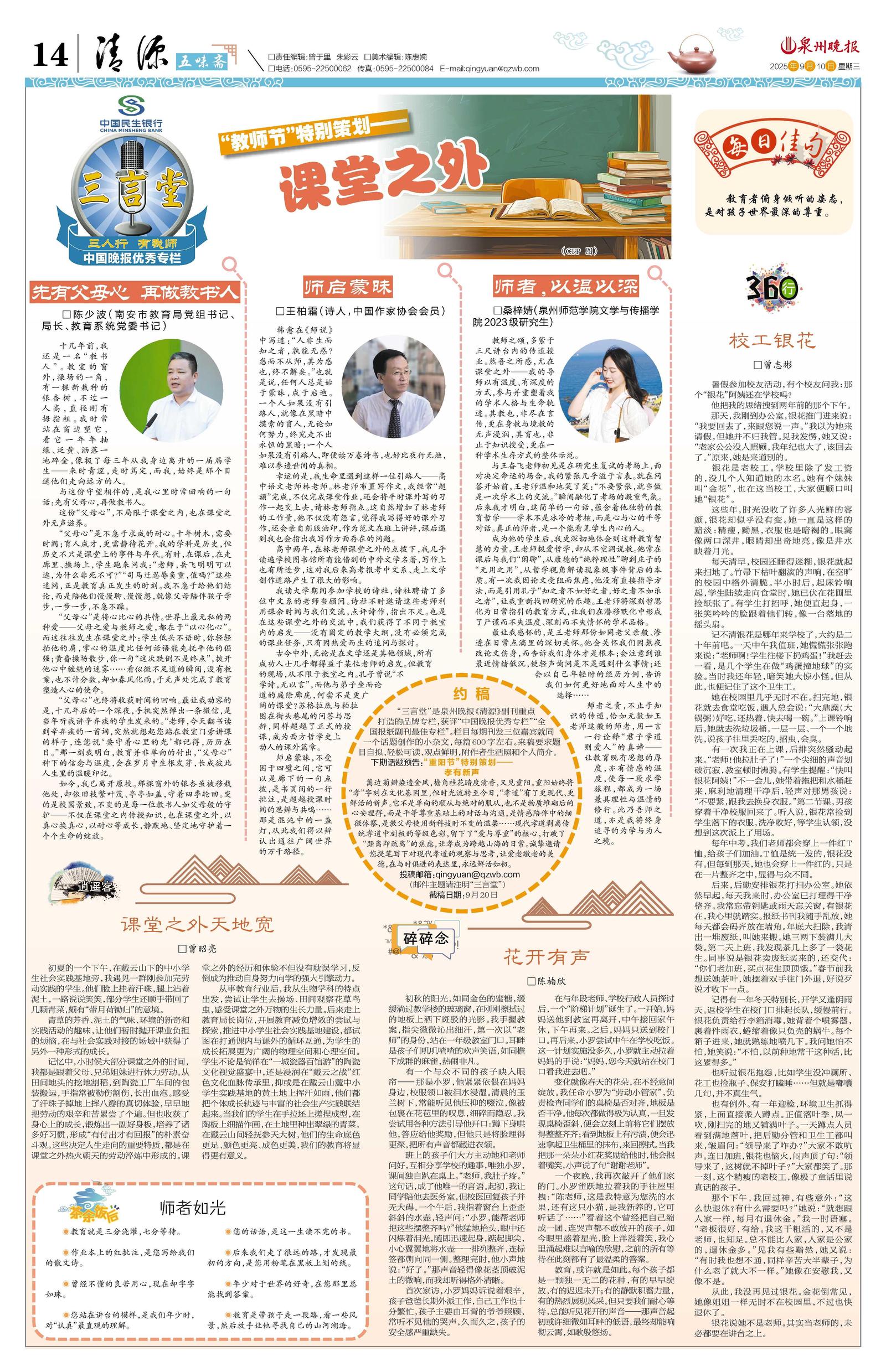暑假参加校友活动,有个校友问我:那个“银花”阿姨还在学校吗?
他把我的思绪拽到两年前的那个下午。
那天,我刚到办公室,银花推门进来说:“我要回去了,来跟您说一声。”我以为她来请假,但她并不归我管。见我发愣,她又说:“老家公公没人照顾,我年纪也大了,该回去了。”原来,她是来道别的。
银花是老校工。学校里除了发工资的,没几个人知道她的本名。她有个妹妹叫“金花”,也在这当校工,大家便顺口叫她“银花”。
这些年,时光没收了许多人光鲜的容颜,银花却似乎没有变。她一直是这样的黯淡:精瘦,黝黑,衣服也是暗褐的。眼窝像两口深井,眼睛却出奇地亮,像是井水映着月光。
每天清早,校园还睡得迷糊,银花就起来扫地了。竹帚下枯叶翻滚的声响,在空旷的校园中格外清脆。半小时后,起床铃响起,学生陆续走向食堂时,她已伏在花圃里捡纸张了。有学生打招呼,她便直起身,一张笑吟吟的脸跟着他们转,像一台落地的摇头扇。
记不清银花是哪年来学校了,大约是二十年前吧。一天中午我值班,她慌慌张张跑来说:“老师啊!学生往楼下扔鸡蛋!”我赶去一看,是几个学生在做“鸡蛋撞地球”的实验。当时我还年轻,暗笑她大惊小怪。但从此,也便记住了这个卫生工。
她在校园里几乎无时不在。扫完地,银花就去食堂吃饭,遇人总会说:“大鼎糜(大锅粥)好吃,还热着,快去喝一碗。”上课铃响后,她就去洗垃圾桶,一层一层、一个一个地洗,说孩子往里丢吃的,招虫,会臭。
有一次我正在上课,后排突然骚动起来。“老师!他拉肚子了!”一个尖细的声音划破沉寂,教室顿时沸腾。有学生提醒:“快叫银花阿姨!”不一会儿,她带着拖把和水桶赶来,麻利地清理干净后,轻声对那男孩说:“不要紧,跟我去换身衣服。”第二节课,男孩穿着干净校服回来了。听人说,银花常捡到学生落下的衣服,洗净收好,等学生认领,没想到这次派上了用场。
每年中考,我们老师都会穿上一件红T恤,给孩子们加油。T恤是统一发的,银花没有。但每到那天,她也会穿上一件红的,只是在一片整齐之中,显得与众不同。
后来,后勤安排银花打扫办公室。她依然早起,每天我来时,办公室已打理得干净整齐。我常忘带钥匙或雨天忘关窗,有银花在,我心里就踏实。报纸书刊我随手乱放,她每天都会码齐放在墙角。年底大扫除,我清出一堆废纸,叫她来搬。她三两下装满几大袋。第二天上班,我发现茶几上多了一袋花生。同事说是银花卖废纸买来的,还交代:“你们老加班,买点花生顶顶饿。”春节前我想送她茶叶,她摆着双手往门外退,好说歹说才收下一点。
记得有一年冬天特别长,开学又逢阴雨天。返校学生在校门口排起长队,缓慢前行。银花负责给行李箱消毒,她背着个喷雾器,裹着件雨衣,蜷缩着像只负壳的蜗牛。每个箱子进来,她就熟练地喷几下。我问她怕不怕,她笑说:“不怕,以前种地常干这种活,比这累得多。”
也听过银花抱怨,比如学生没冲厕所、花工也捡瓶子、保安打瞌睡……但就是嘟囔几句,并不真生气。
也有例外。有一年迎检,环境卫生抓得紧,上面直接派人蹲点。正值落叶季,风一吹,刚扫完的地又铺满叶子。一天蹲点人员看到满地落叶,把后勤分管和卫生工都叫来,皱眉问:“领导来了咋办?”大家不敢吭声。连日加班,银花也恼火,闷声顶了句:“领导来了,这树就不掉叶子?”大家都笑了。那一刻,这个精瘦的老校工,像极了童话里说真话的孩子。
那个下午,我回过神,有些意外:“这么快退休?有什么需要吗?”她说:“就想跟人家一样,每月有退休金。”我一时语塞。“老板很好,有给。我这干粗活的,又不是老师,也知足。总不能比人家,人家是公家的,退休金多。”见我有些黯然,她又说:“有时我也想不通,同样辛苦大半辈子,为什么老了就大不一样。”她像在安慰我,又像不是。
从此,我没再见过银花。金花倒常见,她像姐姐一样无时不在校园里,不过也快退休了。
银花说她不是老师。其实当老师的,未必都要在讲台之上。